诗画论
我说影响是相互的,不是单一的,中国古代的诗论与整个艺术理论、画论是在互相影响中发展的,这种互相影响主要表现在其艺术创作理论及表现技巧方面,它们内容都偏重受庄学禅学思想影响发展形成。
这说来千头万绪,我且按年代举些个例子吧
诗论中的许多美学概念,比如风骨、形神、虚实、体势、神思等等都是从画论中直接移植过来或是受其影响发展出来的。
苏轼说过:书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画在创作的根本原理上是一致的,中国古代最早的画论《庄子.田子方》里说的:解衣般礴,也就是说画家的精神境界应合于道,化于自然。这种虚静、淡、自然,也就是中国古文学对诗人学者在创作中主体精神的基本要求。再有汉代《淮南子》说山训篇里有: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这不就是强调绘画重神似,反对只追求形似,画者谨毛失貌。
魏晋后,画论有更大发展,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中说画要有“奇骨”“天趣”“生气”,这明显影响了其后的“风骨说”。宗炳的《画山水序》说画者的“神思” 要与天地“万趣”相融,这就跟随《文心雕龙》神思篇的意旨相吻了。齐,谢赫综画学理论作中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画论《古画品录》,他提出绘画六法,首为气韵生动,要传的便是“生命的律动”重的是“神”而非“形”。
唐代,最重要的画论家是张彦远,诗论家是司空图。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要画家妙悟自然,物我两忘,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则说:不知所以神而自神,这岂非是一致的。《历代名画记》说“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那是下品,而《二十四诗品》强调诗要吟出“风云变态,花草精神”生气远出,不著死灰,岂非也就是要求诗歌要能气韵生动。张彦远与司空图都是晚唐人,张彦远应是略早与司空图的,从艺术的主体精神看《历代名画记》与《二十四诗品》显然是有内在的思想联系的。
张彦远的绘画美学对唐及后的诗论有很大影响,张彦远主张绘画要心与手统一,而在了然于心(合乎天然的了解,即人在精神上能对宇宙有透彻把握)与了然于手(也是指人为的了解)两者中,了然于心是起主导作用的,后来苏轼的求物之妙要了然于心且也要了然口手就是把其的继承发展与完善。
唐的张怀瓘曾把画分三等,神、妙、能,到了张彦远在其上又添了自然(即逸品),到北宋黄休复则明确地说“画之逸品,最难其俦”所谓逸格即得之自然,出于意表,无非还是说要合乎造化天工,这对后来的诗论影响是很深的,比如苏轼就是把合乎自然作为诗的最高境界。苏轼的画论文论已很难严格区分,他的画论通于诗论,反之亦然。“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也完全适于诗的构思,他的《文说》《书蒲永升画后》一说文一说画,但都提出随便赋形,他那既说画又说诗的“画折枝 ”(全名记不清了)对后世诗论影响极大。苏轼的“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出”怕与顾恺之的迁想妙得,荆浩的凝想形物是脱不了干系的。
说画论自然不可不提董其昌,董完全承袭了黄休复的观点,以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以自然天工为最高,人工雕饰为最下,金圣叹的文章三境很显然也是受此影响的。董其昌在文艺思想上,可以说是对司空图、苏轼、严羽的继承与发展,他推崇苏轼的“崇尚淡泊境界”司空图的“味外之旨”,发展严羽的借禅论诗,也用来借禅论画。他的画论核心在“气韵生动”“平淡天真”气韵生动可说是庄子“天地与我为一”的表现,强调的是如天少而工,老而淡,淡胜工,显然这里又可以看出苏轼“笔势峥嵘,文采绚烂,渐老渐工,乃造平淡。非平淡乃绚烂之极”的影子。而其后郑板桥的“必极工而后能写意”也就是脱胎于此了。董其昌与李卓吾、公安三袁都是很好的朋友,李贽的童心说,公安的“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尤其是袁中道的绘画看法与董其昌如出一辙(袁中道重逸品,推崇水墨渲淡,不屑金碧山水,著有一序文,序名待查)。董其昌的画学思想可以说得是当时以公安派为代表的新文艺思潮的一重要先导。
而在王渔洋的诗论里又可以明显看到董其昌画论的影子。董其昌倡导南北分宗论,重南抑北,实质山水南北分宗的问题,不但是绘画创作及其美学思想上的一大问题,其与古代文艺传统思想也是有极密切关系的。画论南宗重自然天机,北宗重人工修饰,南宗重画外意,若之留白,空非真空,乃神气浮来,生命流动之所,北宗重形体真实细致。实质这两种创作及美学思想的对立,正是六朝“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两种对立美学思想的发展。从南北偏重,可以看出,南宗画受老庄“天地并生,万物为一”“大明”“物化”影响较深,北宗画则受儒家人心感物,功用影响较深。画论南北其实是借禅宗南顿北渐为喻,禅宗南宗讲顿悟,即重自然悟道,天人相契,一朝灵会,不须借人力修行,一朝揭帘,顿窥天下,北宗讲渐悟,也就是要靠人为勤力修行,苦修到家,方能渐悟至理。禅宗南北与画之南北,在思想上有深刻的联系,类的并不仅是形式。
若说玄宰是南宗画论,那么王渔洋可称南宗诗论(只是比方,似无明确术语),王渔洋曾为王揆诗集做过序(《芝廛集序》?待核实),写这篇序的时候王揆的儿子王原祁带去了自己的画,王渔洋的序是先阐述了王原祁的画论思想,再引来讲诗。王原祁画论宗的是董其昌,画师的是王时敏(王时敏画受董其昌影响甚深),王渔洋诗论重“神韵”,就是说要自然神到,神韵超然,绝去斧凿,求天工自然,避人工造作的痕迹,诗要如龙,不必画出全貌,只要点出云雾中一爪一鳞,便神韵宛在,故王渔洋特别推崇郭忠恕的画天外数峰,略略笔墨,使人见而心服,全在笔墨之外,诗文之道,亦是如此,这不是董其昌的“逸品”了。王渔洋强调诗禅一致,得意而忘言之妙境,讲究创作要顺乎自然,心会神至,而不是苦吟强作所得。王渔洋诗化的思想基础也是庄学禅学,这一点和董其昌的南宗画论也是一致的。
清,最重要的画论家首推石涛(道济),他的《画语录》堪称中国古代画论的一个理论总结,他提出一画之法,即心与自然相融相合,也就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意思,创作主体与客体的融一方能进入到最高的境界,这也是脱胎于禅宗妙悟。石涛认为画家的心合乎天地之道,就是绘画的甚尔是一切艺术创作的根本,立了一画之法在于,那么对山川人物,鸟兽草木都可以深入其理,尽其态,这也正是司空图,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概括。石涛在艺术表现上反对死法,提倡无法之法,反对复古的模拟,提倡借古开今,而关于虚实、神形的技巧主张也都是适合于包括诗在内的一切文学创作。
而说到文人之画,古来诗画不分家,大多的文人亦善画,画家亦善文,文人之画,自王维始(写意,前尚有吴道子,但王维开始擅长用水墨渲淡法,不再以设色山水为主,故董其昌南宗以王维为鼻祖),后有董源、巨然、李成、范宽、米氏父子、元四家。北宋,文人画与画院画正式分野,其实董其昌的南北画论,南宗就是指文人画家,北宗即以画院画家为主,文人画家一般不入画院,讲究诗画结合,文人在画上按画意题诗,也常按诗意作画,与画院的画工以画为主不一样(如果子风的专业画家指此类画工的话,上品不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董其昌一力贬斥北宗也是颇偏额的,北宗重精工典雅,山水画风格刚劲凝伟,沉健有力,他们构画自己的意志自然,剪裁天然顺应已心,构图皴法合法度有定法,笔法劲爽刚真,宋徽宗即是,他们也自有其独特的价值)。一般而言,文人画以写意传神为主,体现诗情意诣,追求天工妙趣,逸、神、妙、能,以逸品为先。而画院画以形似为重,多讲究刻画精工细腻,苟有自得,有放逸态则言不合法度,神、逸、妙、能,以神品为先,院画偏设色山水(这不是绝对的,南宗亦有工笔,北宗亦有水墨渲淡,关键在于艺术思想、审美理想偏重各异)如李思训,以金碧山水出名,重色彩浓艳,金碧山水是工笔一派的主要特色,李氏虽重在人工,但亦可达极妙境,那马一角(马远)、夏半边(夏圭)虽说的是李的青绿山水,思想上也重在画院特点,但他们的画也有简淡之趣。
诗画有它各自特殊的表现规律,这约束了它们各自的表现范围,它们不能相代,但它们又可各自将对方尽量吸进自己的艺术领域中。若非要分谁影响了谁,怕是要落了鸡与蛋的窠臼。金大侠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茶、酒、花皆可入武道,盖万流归宗,万物同源也。
我于画道全因当日代人捉刀,方浅浅涉及,本无甚研究,加之连日忙吃,无暇翻典细究,作得粗鄙,引文恐也有失实处,就正诸位。
- 上一篇:中国历代画论集萃
- 下一篇:学习研究中国画论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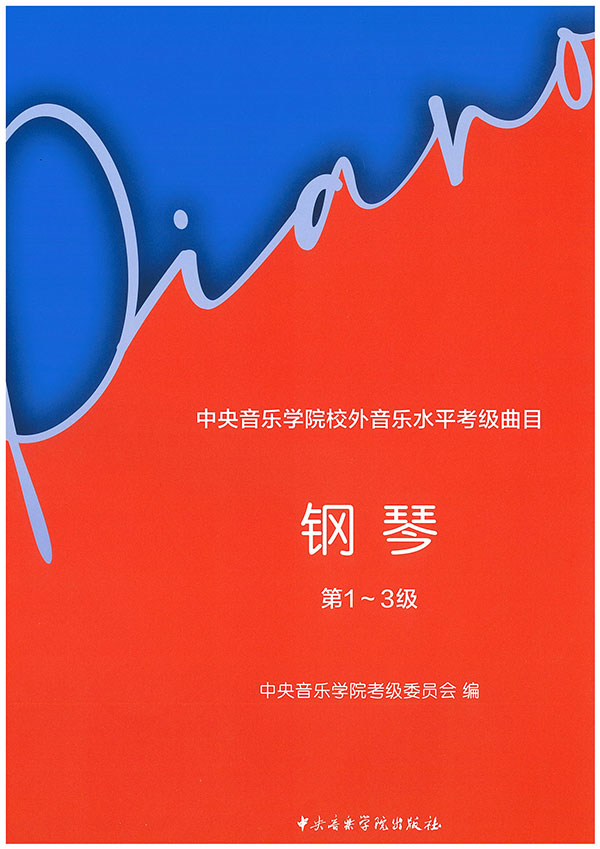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