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伯格:观念的裸体——戈雅与玛哈

戈雅《穿衣的马哈》97×190cm1795-1800普拉多美术馆
首先,她穿着华丽的服饰躺在长榻上:她被称为玛哈,正是因为这套服饰①;然后,同样的姿态,同样的长榻,她赤裸着。
从本世纪初这两幅画首次在普拉多博物馆展出起,人们便开始追问:她是谁?阿尔巴公爵夫人吗?几年前,阿尔巴公爵夫人的尸身被掘出,尸骨被测量,只是为了证实这两幅画的模特不是她!但若不是她,又是谁?我们其实可以轻松地将这个问题作为宫廷的流言蜚语避而不谈。当我们看着这两幅画时,它们确实暗示着一个令人向往的神秘事物,然而,问题的提法总是不对。这不是“谁”的问题。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即便知道了,我们也不会因此增长见识。这是“为什么”的问题。如果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也许会对戈雅多一分了解。

戈雅《裸体的马哈》97×190cm1800-1803普拉多美术馆
我本人的解释是,“无人”为裸体版本做模特。戈雅借助第一幅画,虚构出第二幅。根据面前穿衣服的版本,他在想象中褪去她的衣裳,在布上画下他的想象。看看这些证据吧。
两幅画上的姿态离奇地相似。只有“观念”才能产生这样的结果——“现在我要想象她没穿衣服。”在真实条件下,不同时刻所摆出的相同姿态,总会有显著的差别。
更重要的是那幅裸体玛哈中,她的身体被视觉化的方式。看看她的乳房——如此浑圆、高耸,每只乳房朝外胀开。人那样躺着时,任何乳房都不会呈现出这个形状。在穿衣的版本里,我们找到了解释。紧紧地裹在胸衣里的乳房,确实暗示着这样的形状,因为被支撑着,所以即便人物躺着,乳房也是高耸的。戈雅褪去她的丝绸,露出皮肤,却忘了揣度形状的变化。
上臂也是如此,尤其是前面的胳膊。在裸体画上,这只胳膊肥胖得可笑——如果这也可能——它几乎跟大腿一般粗壮。同样的,我们可以在穿衣的版本上找到答案。戈雅得透过鼓鼓囊囊、打着摺皱的外套去揣测。他没有重构形状,而只是将其简化,于是导致了失衡。
跟穿衣服的版本相比,裸体画上后面的腿被略微转动,转向了我们。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两腿之间便会空出一块,她也不会再有像船身一样的身体。那么,裸体将会因此不那么像穿衣服的版本。然而,如果模特这条腿果真往前挪了的话,那她臀部的位置也应当有相应的变化。而使得裸体的臀部、肚子和大腿犹如在空间漂浮——我们无法确定它们与长榻的角度——虽然后面的腿移了位置,但是前面的臀和大腿绝对仍是直接按照穿衣服的身体所画的,好似遮在身上的丝绸是一层雾,突然被吹开。
确实,从腋窝到脚趾,她的身躯与枕头床单接触的整个轮廓线,在裸体画上是如此失真,而在第一幅画上却是那么真实。在第一幅画里,枕头与长榻时而迎合身体的形状,时而推挤身体的形状:两者相会的线条像是一条线缝——针脚消失又重现。然而,在裸体版本里,这条线缝像图案的破损边缘,它没有现实中的物体及其周遭环境所建立的“施予—承受”关系。
裸体的脸从身体跳脱出来,这不是因为它被作了修改,或是后来添加的(如有些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而是因为它是被看见的,而非画家的虚构。越是看着这张脸,我们便越感到裸露的身体格外模糊,格外不真实。乍看之下,红光焕发的肉体诱使我们以为,这颜色便是肉体的光泽。但是,它是否更接近于幽灵之光?她的脸是可触及的,而身体却不不可。

《戴眼镜的自画像》61.5 ×47.8 cm1800卡斯特尔戈雅美术馆
戈雅是极有天赋的绘图员。他能够飞快地画下运动中的人像和动物,想来他并非一定要参考模特。戈雅几乎本能地了解事物的形状。他对事物形象的谙熟蕴含在他绘画时手指和手腕的动作里。那么,即使无模特,这幅裸体画为什么会如此不真实、如此虚假?
我想,答案应当在他创作这两幅画的动机里寻找。这两幅画很可能是新兴的、令人反感的错视画(trompe-l’oeil)订单的产物——眨眼间,女人的衣服不见了。但是,那时候的戈雅,已不再是默默无闻的画家,不可能随便接受哪个男人愚蠢的订单。因此,如果这两幅画是订单,那么戈雅接下订单时必有自己主观的理由。
戈雅的动机是什么?是乍看之下似乎显而易见的对一桩风流韵事的忏悔或者庆祝吗?如果我们愿意相信裸体画是照着模特所画,或许能使人信服。是夸耀一个实际并没有发生的关系吗?这又跟戈雅的性情不符,他的艺术罕见地不掺入一点矫饰。我认为穿衣的版本是一个朋友(或也许是情妇)随意的肖像画,但当他画这幅画的时候,一个念头突然抓住了他——当她穿着华丽的服饰躺在那里看着他时,他试图想象出她不穿衣服的可能的样子。
为什么会被这个念头“抓住”?男人总是用他们的眼睛脱掉女人的衣服,这是他们假想的一个随意形式。可能他被这个念头抓住,但他害怕自己的欲望?
戈雅有一种将性和暴力联系起来的潜在倾向。女巫题材也是由于这个倾向。他反对战争的恐怖,人们通常认为他的抗议是由于他亲眼目睹了战争地狱般的战场,这是事实。在他的整个良知中,他认定自己是受害者。但他也绝望而恐惧地在行刑者的行列里发现了一个可能的自我。
在吸引着他的女人的眼睛里,同样的潜流变成了冷酷的骄傲。在长着丰满、松弛嘴唇的几十张脸上,包括他自己的,这股潜流变成了嘲讽的挑衅。他正是以极度的厌恶描绘裸体的男子,他们的裸露总是伴随着兽性——就像疯人院里的疯子,印第安人吃人,牧师嫖娼。这股潜流出现在记录暴力狂欢的所谓“黑色”绘画里。但是最为昭然的是他描绘人体的方式。
这一点很难用语言来解释。然而,也正是这一点,在戈雅的几乎每幅肖像画里烙上他的印记。肉体有其自身的表情——正如其他画家所画的肖像有各自的面貌特征。肉体的表情因模特而异,但它始终应着同一个要求而变化:要求之于肉体,就像食物之于胃口。这不是修辞的隐喻。事实如此。有时候,肉体像果实一样泛着光泽。有时候,肉体充满兴奋与喜悦,似乎饥肠辘辘,随时准备吞食。通常——这是他强大的心理洞察力的轴心——它同时暗示着两者:吞食者与被吞食者。戈雅所有畸形的恐惧在此被召唤。他最恐怖的画面是撒旦吃人。
在《屠夫的肉案》那幅普通的画上,我们甚至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挣扎。像此画这样强调一块刚刚还活着的、有感知的肉,如此地符合“屠宰”这个词的情感和字面意义的静物画,就我所知,世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幅。这幅画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不是静物画。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要是戈雅画《裸体的玛哈》,是由于他被自己想象她裸体这一事实所折磨——也就是说,想象她的肉体及其所有的挑逗——我们就能够解释此画如此虚假的原因。他画这幅画是为了驱魔。就像蝙蝠、狗和巫婆,她是“理性睡眠”时所释放的众多妖魔之一。但是,跟其他妖魔不同,玛哈是美丽的,她激起性欲。然而,要将她当作魔鬼般驱逐,用适当的名字召唤她,他必须尽可能地将她的裸体像画得极似穿衣服的肖像。他并非在画一个裸体,他是在画一个穿着衣服的女人体内的裸体幽灵。他用非凡的克制力约束着杰出的创造力,从而如此忠实于穿衣的版本。
我不是说戈雅意图让我们如此解释这两幅画。他期望它们的表面价值为人所识:穿衣服的女人和不穿衣服的女人。我要说的是,第二幅画,裸体版本可能是虚构的,并且因为试图驱逐自己的欲望,戈雅有可能想象地、动情地沉浸在它的“假扮”里。
这两幅画为什么会如此现代?它们的力量,如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正是来自于它们之间微弱的发展。唯一的差别在于她没穿衣服。这一点应当改变一切,但是,实际上它所改变的只是我们观看她的方式。她本人还是同样的表情、同样的姿态、同样的距离。过去时代所有伟大的裸体画都在邀请观者分享她们的青春;她们裸着身体,是为了引诱我们,改变我们。玛哈裸露而冷漠。她好像没有意识到有人正在看她——我们好像正从锁眼里偷看。或者更确切地说,她好像不知道她的衣服已经“不见”了。
在这一点上,正如在许多别的方面,戈雅是先知。他是第一个将裸体画成陌生人、将性与亲密分开、以性的美学代替性的能量的艺术家。打破常规是能量的本质,建立常规则是美学的功能。戈雅有着让他自己害怕的能量。二十世纪后半期叶,性的审美主义维持着消费社会的长期兴奋、激烈竞争和永无餍足的欲望。
①Maja这个女性名是Manola的简写,男性名为Majo,十分普通的西班牙人名,18世纪逐渐成为指代劳动阶层及其服饰风格的专有名词。马德里的贵族女性也开始流行“Maja”的打扮,如简便的裤装等。戈雅画中的女子就是这样一位打扮成Maja模样的贵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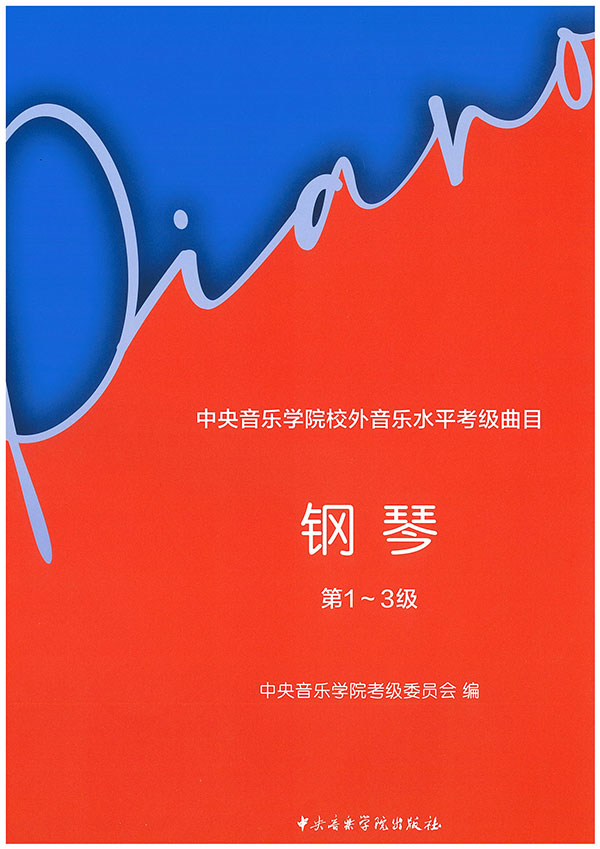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