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画家到情色片摄影 这个女人活成了传奇
世间艺术家千千万,总有一两个活成传奇,卡若琳·史尼曼就是传奇之一,从画家到情色片摄影,从行为艺术家到金狮奖终生成就奖获得者,她的开挂人生是怎样炼成的。

从60年代开始,美国艺术家卡罗琳?史尼曼不间断地进行各类备受争议的艺术形式探索与实验。她的作品涵盖形式广泛,有装置、绘画、拼装、摄影、电影与拼贴画等形式,致力于将女性的身体自主权交还给女性。2017年威尼斯双年展上,她被授予金狮奖终生成就奖。
对于美国艺术家卡若琳·史尼曼(Carolee Schneemann),美国学者艾莉森·格林(Alison Green)评价道:“我是在上大学期间学习艺术史的时候了解到的这个艺术家。但真正令我印象深刻的,是6、7年前我在参与研究1959年至1960年美国艺术史时读到的一篇关于她早期画作的评论文章。我从来没有想到卡若琳女士在已是知名画家的时候会停止画画,选择去当一名行为艺术家。这个行为在当时看来的确是挺让人难以理解的。然而,去探索让一名画家选择放弃绘画,转而寻求别样艺术表达形式的原因是一项很重要也很有意思的工程。

我因此做了很多研究,也与卡若琳女士进行了交流。结果我发现她一方面倾向于用各种技术展示艰涩难懂的冲突矛盾。在某些时候,行为艺术于她而言更是一种用肉体表达思想情感的工具。卡若琳女士会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去向世人展示世界,并通过行为艺术在她的影像作品中展现出来。这也正是她与众不同的地方。另一重方面,卡若琳女士的作品有较强烈的政治意味,这一点在她60年代的作品上表现得尤为强烈。时至今日,她的作品仍然含有较强的政治隐喻含义。卡若琳女士如何在作品创作和个人表达之间做出选择和协调,她的作品对她个人思想有怎样的映射,在各种复杂条件下她是如何协调工作和生活?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探讨。”

不论别人怎么说,大家要记住:我是一名画家,不论怎样我都是一名画家。直至我死,我仍旧是一名画家。所有我在视觉行为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一切表达方式和技巧,全部都归功于我当初获得的绘画训练。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源于以前的绘画经历。

绘画这个概念从我用身体作为表达媒介开始而逐渐变得模糊起来。而我将身体作为艺术表达媒介的行为却也不断给我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从某种方面来说,这是对于传统绘画技巧里的意象表达的一种讽刺。准确来说,与委拉斯凯兹一样(Velazquez,巴洛克时期西班牙画家)使用画笔进行绘画创作,我感受到了画笔与画纸之间的强烈触感,我也逐渐意识到画笔其本身就是一种视觉媒介。而我则想要加深和强调这种触感,将之应用在艺术行为上。如果回溯过去,我可以说这个发现拓宽了我对艺术世界的了解,并且深深影响了我。它们促使我对历史中的女权问题、对社会取代和压抑女性的一面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并将它们表达出来。我想强调的是:我所能做的是激发一个集体、一群人,与那些想要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具象化、表达出来的人一起合作,去参与、去记录他们的所见所想。要知道当时想要组织这么一场活动,是会遇到很多现实问题的,更不要提他人的反对。在那一伙人中,就有一位男士否认邀请了我,并且明确表示不希望由我来记录他们的谈话。对我来说那天真的是一场噩梦:男士们在进行激烈的讨论,而我完全找不到头绪。

我很高兴能和很多很厉害的人一起合作。当时整个集会持续了有1到2周。它本质上就是一群人在不停地讨论和辩论。在我的小组中有两匹马拉着一辆汽车,汽车上坐着人。就这样把人拉到这里,然后又拖到那里。在影片中还附有人们当时的对话字幕。在声音的辐射下,这一切就如同催化剂一般,催化人们内心的自我辩论。
我大概从1965年开始拍摄所谓的“情色影片”。我们本想在那里拍摄《融化》(Fuses),但是活动组织者咨询了他的律师顾问,然后找上了我们。他把我拉到了圆屋边的一处垃圾堆旁,警告我们如果拍摄这些影片就会让警察以宣扬淫秽色情信息的缘由逮捕我们。而且集会里所谓的自由人士也不会为我们说好话。

这一次在国家电影剧院(National Film Theatre)的表演可以说稍稍搅乱了这个圈子。某种意义上来说,地下影院第一次以这种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我在尝试着构造一种视觉模型,让它与影片行业框架固有的一些特性进行对抗。我十分想要打破那些固有的规则,挣脱这些束缚。特定的保护与要求、对于观众的要求都值得我们去重视。不用说,动力剧院(Kinetic Theatre)的表演再次震碎了人们的三观。我们准备了很多气球还有一个鼓风机。我们会给这些气球充气,让它们胀得很大,大到能把观众挤出展览房间。这个行为表演很有趣。在赤身裸体的行为艺术结束后,这些气球会变大,到处乱飞,逐渐占据整个空间。然后观众就不得不往外跑。这一整个行为我把它归到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和运动学领域。
我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学的是风景画。可我那会觉得绘画本身并不足以支撑绘画自己。在那时,这个想法对于一个年轻的艺术家来说实在是太存在主义。我那会和我的一个同伴住在一起。我们居住的房子周围有很多树,还有湖泊。有一次,一场龙卷风袭击了这里。一棵大树被连根拔起,被龙卷风甩到了我们这里。我们的厨房被这棵树生生地分为了两半,到处都是散落的树枝和碎屑。我们都惊呆了。而我们的房东已经88岁高龄,什么忙也帮不上。就在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的猫慢悠悠地走了出来。因为厨房的门已经被毁,它可以轻松无障碍地穿梭于它的领地和厨房之间。当时看到这个场景,我心里一动: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我想和这只猫做一样的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设置了具有破坏性美感的场景,叫了几个学生过来。在这堆残渣中像那只猫一样用自己的身体在废墟里到处游荡,体会每一处毁坏的角落。就这样,我们开始了这场行为艺术表演。
我们现场表演的音乐不算是传统意义上的音乐。那是一些刮擦声、塑料袋摩擦声等等声音的混合体。音乐制作人很好地把它们结合在了一起。我和他很早时在伦敦合作过,那会我还搭帐篷睡在他们影片制作人的地方。那会的影片制作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地方。回到话题来,我更倾向于这是“声音”而非“音乐”。

《水光》(Water Light Water Needle)的灵感源于威尼斯,后来就在纽约的圣马克教堂(St. Mark's Church)进行了表演。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图片都重新进行了修订和整合。图片背景源于新泽西的一处废弃村庄。这个作品是受到很多事物启发后创作而成的。水天一线、干湿交界、人影慢慢消失在湖光潋滟之中。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场景就仿佛被催眠,迷糊回到了威尼斯水城。在纽约圣马克教堂表演时,观众们就坐在我们装置的各种绳索之下。现在想来还是挺危险的。我们当时本想在室外进行这个表演,但是我们的经费严重不足。有一个一直在帮我们整理这些绳子的小孩子,他说“我也许能给你们推荐个不错的地方,不过它在郊区。”我应好,然后我就跟着他去了。巧合的是,这孩子的父亲是一名威尼斯籍的精神病学家。所以最后就有了这些和我们的绳索完美结合的树木。我们这次有拍影片来记录整个过程。由于设备到位,直到过去的五年里,我才有机会重新整理剪辑我以前的那些影片。
至于为什么在一个教堂里表演,这是有缘由的。这样的行为其实是很有风险的。在60年代,圣马克教堂和贾德森教堂(Judson Church)为他们各自的社区团体服务。这些群体都是一些吸毒的人,还有一些诗人、艺术家和流浪汉。我们团队冒着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来到这里追求艺术的极致。所以相对来说,呆在教堂里就算是比较安全一点了。除此之外,我就不得不说说伦敦那座被我们毁了的教堂。1964年的时候,巴黎有个关于自由表达的节日。那会有个看起来神经兮兮的冰岛艺术家给我拍摄了一套影片。他希望我去尝试参加一下巴黎的那个聚会。我那会大概24,25岁,又特别想去。所以那位艺术家买下了我一副作品,这笔钱就刚好够支付去巴黎的单程机票钱。虽然我父亲后来给了我一些钱,但都是一些来自奇奇怪怪地方的钱,根本用不了。我最后在巴黎身无分文,不得不向他人打电话求助。不过整个旅程里最令我开心的,就是那一场在伦敦教堂里的表演。
在伦敦的那场表演真的是一团糟。预定的演员变成了一群拿着曲棍球棒的小姑娘;我的经纪人喝醉了完全走不了路;有一只用于表演的鸡卡住了。到最后,鸡肉的各个部件散落在修道院各个角落。整个混乱的场面让主事人开始变得神经紧张。他一会向那边喊停,一会又忙着叫人清理垃圾,一会急着把人赶出教堂,一会又要我们把一些人塞进电梯,关到教堂顶楼去。后来我们就被赶出了这里。我被他们丢进车里,他们把一张毯子扔在我身上。然后我就开着车到处闲逛,最后醉倒在教堂附近的一个酒吧里。

我现在做关于塞尚(Cezanne)的研究和演讲。我觉得风景画和它表现形式之间的联系意义重大。1968年那场表演中,我打扮成一个农民,没有穿任何内衣内裤。口袋里有一大堆的橙子。在演讲中,一边展示着画家塞尚的画作,一边向观众扔橙子。有一次我让我男朋友用墙纸把我全部糊上。然后我们又准备了很多报纸放在台下。我们邀请了2到3个观众上台再次把我全部糊上,然后推下台,我就倒在那堆报纸里。当时在场的人对这次表演的评价都很不好。有一个老上校还说这是只有精神错乱的色情狂才能做出来的事情。这很明显不是正面评价。所以也许我们的作品中的确存在着一些消极的因素。
关于教堂那一次表演,我将它归结于灵性,虽然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禁忌。过于在乎这些宗教甚至是道德上的禁忌的话,这些超自然现象本身就会给自己的工作生活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困扰。这是我们的文化中,既唯心又唯物的一部分。我不能说我的行为是在否定这些传统观念,但我会努力将我的工作与之协调。有机会也会去构想一下这些不可见魂灵的面貌。

对于911那场袭击,我的第一反应是:若不是有同谋,这些自杀式飞机是怎么越过我们的领空警戒对我们进行袭击?我禁不住想: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牺牲?这场袭击给政府带来了什么教训?它又改变了我们什么原则?在处理图片的时候,我的这些所想却变得简单了。如果我在用电脑处理图片,图片是由无数的像素格组成;如果我在报社工作,我可以把这张图片不断缩小放大。但我却不能对一个视频做出相同的处理。所以我要赶在政治施压删除图片前找到并保存这些图片。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活计。所以我在想,我们是否能够回归到“历史是万物”的想法上去。这一次只是小部分历史的循环。然而对女性来说,历史却总是一直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
《终端速度》是一个复杂的装置,里面有很多复杂的结构。它的灵感来源说来容易。一次我在街上走着,然后看到了一个特别古怪的东西在动。它看起来就像一个机械手臂。我回家,然后把它画了出来。后面就是制作的过程了。我想要这个手臂可以前后摆动,然后我们画了很多草图,还通过计算机进行模拟,在各种程序步骤之下最后终于得以实现。这个作品总是让人感觉它带有敌意。而且我觉得它太早就被展示出来,当时还不是时候。普通大众看了展览以后,只会谴责艺术家在利用悲剧卖惨、博同情赚钱。
尽管我很喜欢与前面提到的男性电影人、制作人进行合作,和他们合作讨论的氛围也很融洽,但在60年代和70年代,他们仍然是任何事情、任何群体甚至是任何讨论集体的中心。我喜欢伦敦。由于受到越南战争的影响,我刚到伦敦的时候心理状态很不好。当时的人们也很难意识到文化压力之下的重重压力、冲突和矛盾。在那个年代,女性艺术家面临重重阻碍。那是一个男人可以毫不害臊地说出“女人画画就如同猴子演奏小提琴”的年代。虽然人们不停地和我说我可以做任何事情,但这不代表我真的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然而在阅读小说的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透过作者的视角去享受一下他眼中的世界。然而我又不得不睁开眼接受现实的冲击。然后自我思索:你能接受这个表演吗?是否能理解里面的理论?能否接受这个与正常大众所期望的女性形象千差万别的演讲者?

我以前常沉迷于在艺术展览馆里游荡。我不仅仅是因艺术实验室和里面的作品而着迷,我更喜欢的是个人对于自己已有作品的再想象和再创作,那是就我所想要的结果。但与此同时,我也会去反面思考我这么做是否有什么弊端。人们之间相互影响,我们同样需要别人的作品来给予我们刺激和启发。这种启发和刺激务必要足够新鲜和有力来提供一定的导向,而不是贫乏的简单思考入门和构想。它们要能够有特定的影响,并指引向独一无二的方向。我觉得嘎嘎小姐(lady gaga)就是这么一个对源自于我的启发进行了重新整合的一个优良例子。大家都知道油管(YouTube)上有这么一个视频。一位来自水牛城的女子在卫生间里对着相机镜头说道“我要吃了我的卫生棉”。我也不明白她问什么要吞下带血的卫生棉条。我其实接到了几个来自伦敦记者的电话,他们强烈建议我看看这个视频并且谈谈我的看法。我只能说,她的行为让她与她的身体进行了一次亲密的接触,这是一场很美妙的行为。
我大概从1975年或是1977年开始就没有再进行行为艺术了。而我从70年代起就不再将自己的身体作为艺术媒介。要知道,艺术媒介数不胜数。我也在尝试使用新的媒介。不过现在也还是有很多女性艺术家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媒介,直至老去。在50年代后期,我在读研究生,和我的室友挤在小小的房间里。房间里每天充斥着不同的音乐。虽然我是个画家,或是行为艺术家,但音乐给我提供了数不尽的灵感,对我思想系统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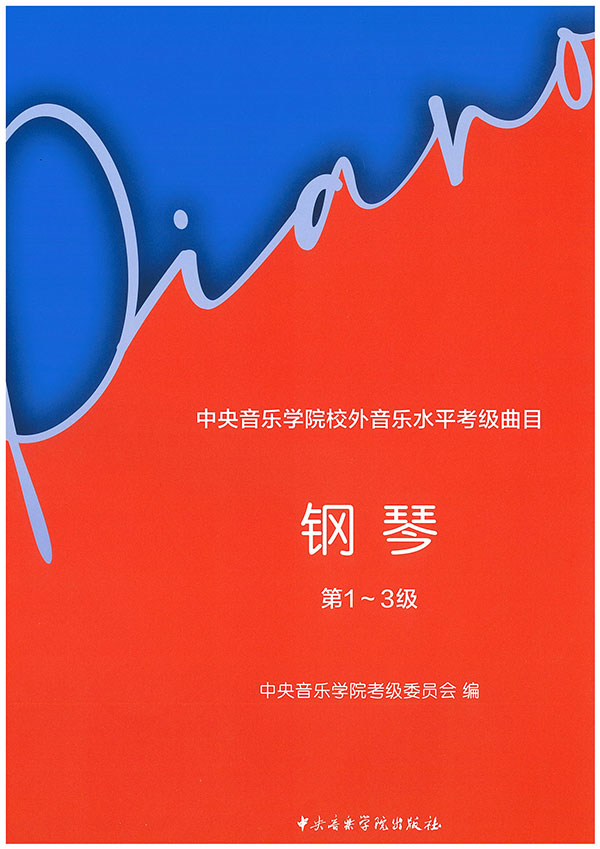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