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世界角落与这些艺术大师,谁成就了谁?
米勒选择了巴比松,莫奈选择了吉维尼,梵高选择了阿尔勒,高更选择了塔希提岛,马蒂斯选择了丹吉尔,达利选择了利加特港……故乡不能选择,栖居地却是可以选择的。在你所意想不到的世界角落,艺术大师曾驻足停留,少则一年半载,多则数十年、大半生。
这些世界角落与这些艺术大师,谁成就了谁?生活在别处,不少艺术大师找到了灵感的爆发之地,艺术的盛放之地,甚至是精神的原乡。而因为艺术大师烙下的印记,很多原本寂寂无名的地方如今闻名遐迩,吸引着众多艺术爱好者前来“朝圣”。

高更在塔希提岛留下的画作至今还在以肆无忌惮的色彩、野性神秘的气息刺痛着人们的眼睛,其中就包括这幅《大溪地之山》。
高更在塔希提岛:自由地去爱,去歌唱,找到饱满的生命哲学
1891年春天,43岁的高更从马赛出发,独自一人到南太平洋上的蛮荒之地塔希提岛(又名大溪地)去。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远行,高更出售了30件作品筹集路费,象征派诗人马拉美在巴黎伏尔泰咖啡馆主持宴席为他饯行。在南太平洋岛屿,高更一待就是十多年,直至生命尽头。这里的异域风情与土着女子,让他找回绘画的激情和冲动,留下绘画生涯最灿烂的一笔。时至今日,这些画作还在以肆无忌惮的色彩、野性神秘的气息刺痛着人们的眼睛。
曾经的高更,是巴黎的一名证券经纪人,稳定安逸,收入颇丰。35岁那年,他却不靠谱地选择成为前途未卜的全职画家。有生之年,高更算不上十分成功的画家。尽管他混在印象派的队伍里,参加过4次印象派画展,但身份始终边缘———莫奈不愿与这位“信手涂抹的家伙”握手,艺术评论家称他只是跟在毕沙罗后面的业余画家。
赴塔希提岛以前,高更就曾脱离印象派,在法国境内的布列塔尼、阿尔勒等地开始漂泊的绘画生涯了。最终诱发他流浪到天涯海角的导火索,可能就是梵高,是与梵高的交往加剧了高更对现实的恐惧和对与世无争世界的向往。在阿尔勒,高更与梵高共同度过惊心动魄的62天、酿成轰轰烈烈的“割耳事件”以后,分道扬镳。梵高走向他愈加疯魔的纯粹世界,高更则开始了在塔希提岛的自我放逐。临行前他曾表明心迹:让其他人去拥有荣誉吧!我只追求安静平安,法国的高更从此逝去,你们再也见不到他了……我终于获得了自由,不需要再为金钱而奔波忧虑了,我将能够自由地去爱,去歌唱,去死亡了!
初踏塔希提岛,强烈的阳光、浓密的森林、头戴花环有着小麦色皮肤的女人们、原始与未开发的纯真都令高更沉醉。在这里,他建了一间原始竹屋作为自己的工作室,按照当地习俗娶了土着少女特哈玛娜为妻,劳作、画画、书写……这是他的流金岁月。在他于塔希提岛留下的散记中,他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离开是为了寻找平静,摆脱文明的影响。我只想创造简单,非常简单的艺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回归到未受污染的大自然中,只看野蛮的事物,像他们一样过日子,像小孩一样传达我心灵的感受,使用唯一正确而真实的原始的表达方式。
1893年,高更也曾短暂地返回法国。他带着于塔希提岛创作的数十件作品到巴黎一家画廊办展卖画,想要赚点生活费。结果却是每天站在画展现场,听着参观者发出的嘲笑。莫奈、雷诺阿、毕沙罗等人甚至认为这些画糟糕透了,太粗野,太原始,而这恰恰是高更追求的。大失所望的高更,看清自己是巴黎生活的局外人,一年半以后重新踏上去塔希提岛的路途。这一离去,真的成了与文明世界的永别。高更再也没有再次踏上欧洲大陆。
在塔希提岛,高更主要留下了鲜明的两类作品。一类着意于表现当地妇女闲适朴实的生活,粗野却健康的美,极富异域风情,另一类用土着人的形象标示基督降生、天使、亚当与夏娃等,充满神秘主义的情绪与意象。在这里,高更找到了内敛而饱满的另一种生命美学。
生命的最后几年,高更其实在以发狂的创作与残酷的命运搏斗。盛放的艺术背后,有着人们难以想象的穷困潦倒、心力交瘁、疾病缠身,甚至精神的几近崩溃,他曾怀疑一切事物,且一度服下砒霜。高更在南太平洋岛屿完成的一生中总结性的作品———长约4米半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就来自他有生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精神危机———听闻最心爱的女儿阿丽娜死于肺炎。
今日此地:如今的塔希提岛是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岛上高更曾经住过的“欢愉小屋”,成了高更博物馆,让高更的一生在那些画与故事里得到复活。

阿尔勒的田野风光被梵高用画笔定格在《阿尔勒的鸢尾花》
梵高在阿尔勒:追寻太阳的足迹,将调色板上的亮度不断上调
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阿尔勒镇,梵高度过了一年又3个月。梵高艺术创作生涯最璀璨的火花,却正绽放在这段不算太长的时间里,留下200多幅画作,包括《向日葵》《自画像》《播种者》《阿尔勒的舞厅》《夜间咖啡馆》等名作。
1887年秋天,出于对巴黎社交生活的厌倦,梵高决定离开。他认为自己不是城市画家,他的天地在田野与荒地。梵高想要寻找的,是一个有着炽烈太阳的地方,一个能将其调色板上亮度不断往上调的地方。他心里有团熊熊燃烧的烈火,随时窜出来呼应太阳的升腾。有人建议他去阿尔勒,说那里的景色与非洲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阳光充足,干燥少雨,是画家们的天堂,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能经得住阿尔勒太阳炙烤的画家。
梵高是1888年2月到达阿尔勒的。这里的阳光果然猛烈、刺目,似乎将一切照透,映出了万物的本质———一种通透的、灿烂的、蓬勃的生命本质。这给了他空前的喜悦与无限的灵感,梵高的创作进入“疯狂”。繁花盛开的果树、开满黄紫相间小花的田野、繁星闪耀的夜空、成熟的麦田等等,四季更迭的种种景致都令他感叹“根本无法抗拒继续创作的诱惑”。渐渐地,他找到了一种既属于阳光也属于他自己的颜色———夺目的黄色。
在阿尔勒租住的“黄房子”,成了梵高内心的栖息地。这是位于拉马丁广场2号一座建筑物中的房间,因为楼房外壁被涂成黄色而得名。梵高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装点着自己这个新家,并梦想着将它变为艺术家的乐园。他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反复提到自己的房间以及“画家之家”的蓝图:“我想让它真正成为‘一间艺术家之屋’———没有什么昂贵的东西,但是从椅子到图画,每一样东西都有特色”“至于床,我已经买了乡间常用的床,不是铁床,而是大的双人床。它的外表给人坚固、耐久且恬静的印象”“房子给我带来了安逸感,从现在起,我感到我正在为未来工作”……
梵高以“光之屋”来称呼“黄房子”———黄色象征着爱的最高闪光。他似乎把对于尘世的爱都留在了“黄房子”,还曾兴致勃勃地游说同为艺术家的友人高更来此与他为伴。梵高现存的画作中,至少有5幅在描绘这个房间,就像他自己的描述,“颜色在这里代表一切:墙壁是淡紫罗兰色,地板是红瓷砖。木质的床和椅子,就像新鲜的黄油;床单和枕头拥有柠檬般的淡绿色……这些物件带来的,也是一场休憩、或说是梦。”
阿尔勒的一家医院,梵高也住过好一阵子。在与高更闹掰,割下自己的左耳之后,梵高被送到了这里。住院期间,他画下了医院的病房与庭院,画面和线条越来越扭曲。
今日此地:弗洛姆广场上梵高画作《夜间咖啡馆》中的那个黄色咖啡馆,如今已经重建并改名为梵高咖啡馆。梵高割掉自己耳朵之后逃避疗养生活的那家医院,如今辟为梵高艺术中心,花园的花卉格局维持着梵高画中的模样。
达利在利加特港:画中的梦境、笔下的扭曲,原来都有迹可循
西班牙的小渔村利加特港距离达利的故乡菲格列斯,并不算远,它们几乎只隔了一座圣皮埃山。利加特港的波谲云诡、怪石嶙峋,却与菲格列斯稍显平淡的景观迥然相异。在利加特港南面一座傍海的古怪屋子里,达利度过了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与他一生的挚爱加拉。他大概也不曾想到,日后正是这里的风景激发了自己最为奔放的想像力———原来达利画中的梦境、笔下的扭曲,都有迹可循。
达利与加拉是私奔到利加特港的。加拉比达利大9岁,初初与达利见面时,她还是一位法国诗人的妻子。达利的父亲当然怒了,写信通知将他逐出家庭,这意味着达利再也不能从家里获得经济上的支持。达利买下利加特港某个小海湾里的一间逼仄且破旧的木板屋,与加拉一起设计了房子里的每一个细节,并找来木工将他们的想法付诸实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日子有世外桃源般的浪漫,现实也提醒着他们,这里是世上不毛之地中的一块,用达利自己的话说,“早晨是充满朝气的阳光,傍晚却是令人心酸的悲哀之感”。
除了西班牙内战期间曾移居海外,从1930年直至1982年加拉去世,达利每年都要在利加特港的小屋住上很长一段时间。达利曾在自传中写道:“我了解它的各个角落和隐蔽之所。我记得它的小湾,它的涯角,它的峭壁的形状,我在这儿留下了我整个感情和爱情生活的印迹。”
事实上,达利在利加特港留下的还有很多名作。他不少画中的梦境、笔下的扭曲,原来有迹可循,那正是利加特港特有的风景。利加特港有个叫做十字架海角的地方,在风和海的侵蚀下,海边的天然岩石不仅陡峭,还被雕刻成狮子、骆驼、鹰等千奇百怪的形状,这道颇有辨识度的海岸风景线激发了达利最不羁的艺术想像力。达利的名作《永恒的记忆》中,远景的峭壁就来自利加特港。而在他名为《利加特港的圣母》的作品中,加拉的形象也置身于利加特港的风景中。
今日此地:昔日达利与加拉隐藏在山谷中的秘密爱巢,如今改造成了达利故居博物馆。这里保持了达利和加拉居住时原有的陈设,各种装饰品与家具奇特怪异地组合摆放,房子的结构弯弯曲曲,如同绕不出的迷宫,一切充满超现实主义的奇幻色彩,仿佛将艺术大师的奇思妙想化为现实。

莫奈的吉维尼不是只在人们熟悉的“睡莲”系列、“日本桥”系列、“紫藤花”系列中,还有这幅《春天的吉维尼》呈现的明媚春光。
莫奈在吉维尼:养花侍草造园,对光线的研究达到极致
距离巴黎仅有70公里的小镇吉维尼,位于爱蒂河与塞纳河汇流处,有着明媚的风光。莫奈在这里安享晚年。
1883年4月的一天,莫奈乘坐从维尔侬到加斯尼的小火车,途经山花烂漫的吉维尼,就像“一见钟情”的少年,欣喜若狂。他冲动地租下一幢房屋,将全家搬迁于此,一住竟是40多年,直至去世。
莫奈一生中最满意的作品不是他的画,而是依照自己的审美在吉维尼一手造起的新家———吉维尼花园。在这里,他过着养花侍草的“花痴”生活,依照花木自身的生长形态来设计花园,也格外重视色彩的协调性,园子里高低错落、不同色调的植物摇曳出自然的视觉动感。他甚至考虑花的生长期,以便花园一年四季有花可赏,时时充满生机。挖坑引水,种树修桥,莫奈还将早年最重要的两个主题水和花卉集合在一起,建造了一个绝妙的水上花园。这里静谧、悠远,湖里种满了睡莲,岸边则是垂柳和竹林,绿色小桥跨于如镜的池水之上,天光水影构成心目中最理想的印象。
旖旎的吉维尼花园,成就了莫奈创作上的黄金时期。当时,莫奈对光线的研究达到了极致,日后为他赢得最多盛名的“睡莲”系列、“日本桥”系列、“紫藤花”系列都诞生在这里,在不同季节、天气、光照之下,塑造同一个场景的不同形象,捕捉一刹那光线的变化。
今日此地:如今的吉维尼因莫奈的花园而闻名,昔日的莫奈故居成了一座博物馆,保持着艺术大师画中的样子,每年吸引众多艺术爱好者前来观光。

马蒂斯在摩洛哥丹吉尔法国大酒店画下名作《窗口望去的风景》
马蒂斯在丹吉尔:画风突变,别样的才思被异国文化激发出来
1912至1913年,马蒂斯两次前往北非的摩洛哥,总共停留了7个月,其中在摩洛哥北部古城、海港丹吉尔留下最多的足迹。1910年冬赴西班牙伊斯兰文化区时所受的吸引,促使马蒂斯决意到更远一些的摩洛哥深入探索异域风情,以期异国文化激发出自己别样的才思。
摩洛哥之行对马蒂斯的创作的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创作出24幅画作和不少图纸,在画布上尽情挥洒着对混杂辛辣阳光、咸涩海风的异国风情的热爱。
在摩洛哥,马蒂斯的画风发生了突变。他开始把纯黑作为一种光的色彩来使用,而非黑暗的色彩,用色变得极其大胆。这是他捕捉重塑摩洛哥阳光的方法。受到摩洛哥文化的影响,马蒂斯也热衷起结构、线条和纹样。有人说,摩洛哥留给马蒂斯的,不仅仅是一个彩色的国度和激动人心的风景,同时也是他精神性的体现。
到达摩洛哥,马蒂斯才意识到找到一个女性模特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伊斯兰妇女都是披戴面纱的。终于,一位名叫索拉的妓女愿意充当他的模特。尽管索拉愿意裸露自己的身体,马蒂斯却选择让她身着保守的服饰,用审慎的姿势端坐在画布前。除去对性主题的依赖,马蒂斯被认为迈出从自身早期现代主义中突破的一大步。
这一时期马蒂斯的风景画也呈现出超脱世俗的宁静。《窗口望去的风景》中,窗台上摆放着两盆植物,窗外蜿蜒伸向远方的小路,稀疏的行人,隐在茂密树林的房子,无不让人嗅到空气中的宁静气息。在《摩洛哥的咖啡馆》,几个穿着民族服饰的画中人,或坐,或躺,或凭栏,或望着鱼缸中的金鱼,这似乎反映出马蒂斯心中的理想———创造一个愉悦、和谐、优雅的世界。
今日此地:马蒂斯当年在摩洛哥丹吉尔法国大酒店画下名作《窗口望去的风景》的那个房间,如今成了迷你马蒂斯博物馆,房间里处处挂有马蒂斯的画作。从那间画室往外看去,就是他画笔下的异国情调。
米勒在巴比松:在袅袅升起的炊烟中,收获艺术创作的硕果
米勒1849年来到巴比松,一个巴黎南郊约50公里处的森林村落。本想小住几周,结果举家迁来,一住就是27年,直至自己生命终了。
此前12年,米勒在巴黎过着“水土不服”的日子:穷困潦倒,常常被讥讽为“乡巴佬”,为了生计,不得不画一些迎合市场自己却毫不喜爱的题材,也曾因罹患热病一度濒临死亡。一天,他偶然听见一位路人正指着橱窗前自己的一幅画作对身旁的朋友道:“这就是那个除了画裸体,别的什么也不会画的米勒。”这话犹如当头棒喝,米勒决意改变。
而巴比松像是米勒重生的起点。质朴的田园风光与日常的生活情趣,才是属于他的精神原乡。在这里,米勒过上真正属于自己的农夫生活,享受到一种真正的乐趣。对于这段生活,米勒曾经这样自述:“我不知道圣母院与市政府办庆祝大典是何等盛大,但我喜欢简单隆重、不甚铺张的生活。对于一个赶回家的疲倦农夫来说,看到自己家屋顶上的烟囱在晚霞中袅袅升起的炊烟,还有在偶然的某个傍晚看到的落日余晖和云端闪烁的星光,在草原上晃动的人影,听到马车的辘辘声,流动商贩的音乐与大家所宠爱的许多事物,是多么幸福啊……”
巴比松更是让米勒迎来艺术创作上的春天。《播种者》就是他落脚巴比松之后创作出来的第一幅激动人心的作品,只见苍凉的麦田里,播种者阔步挥臂,撒播着希望的种子。之后的《拾穗者》《晚钟》《牧羊女》等作品也都因表现人与土地、与生存的息息相关,获得一种穿越时空的永恒性。
今日此地:巴比松的很多房子如今成为了画廊,展览着当今流行的各种风格流派的绘画。很多房子的外面都刻有石碑,标注某位着名画家曾经住在这里,其中米勒故居保留得最为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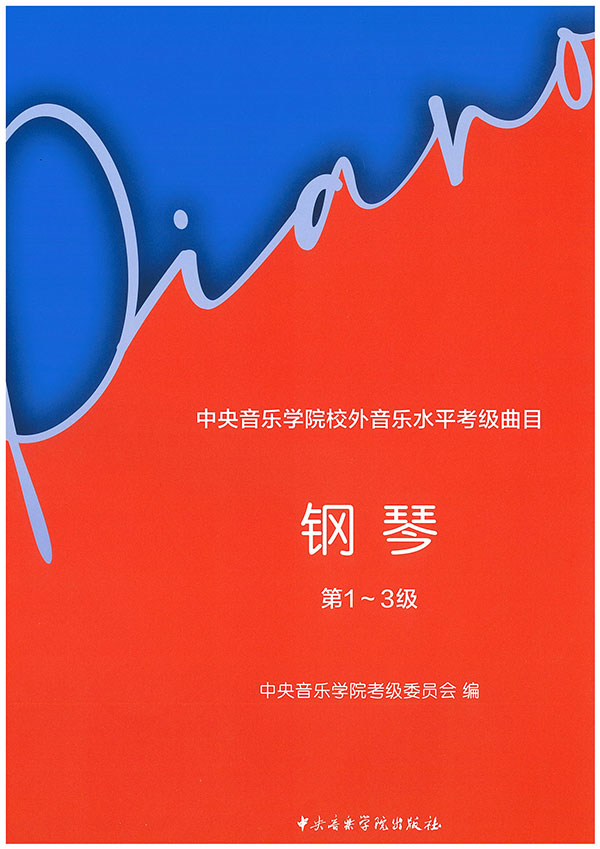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