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翟永明:全中国的摄像头都是我们的摄影师
昨天第七十届洛迦诺电影节落幕,本次入围国际主竞赛的两部华语影片无疑都成为本届洛迦诺最引人瞩目的亮点。王兵纪录片《方绣英》拍摄了身患老年痴呆的方绣英生命最后的日子,以及她的家人,村里的朋友在最后这段日子里和她的相处方式,以及他们各自的生活。影片最终获得了70周年洛迦诺的最佳影片金豹奖。这也是继1992年罗卓谣《秋月》,1998年吕乐《赵先生》,2000年王朔《我是你爸爸》,2009年郭小橹《中国姑娘》,2010年李红旗《寒假》,华语电影第六次斩获洛迦诺最高大奖。
而由著名当代艺术家徐冰导演,诗人翟永明、导演张憾依编剧的《蜻蜓之眼》则成为本届洛迦诺电影节话题之作,这部完全用监控录像剪辑而成的电影,把监控下每一个中国人都变成了演员,无疑是今年洛迦诺影评人们热议的焦点。最终影片也成为影评人心目中最佳影片,收获了费比西影评人奖以及天主教人道精神提及奖。
在洛迦诺期间,深焦DeepFocus专访徐冰、翟永明这对初入电影圈的跨界艺术家,并通过这个访谈为我们读者介绍这部华语电影史上独一无二特别电影。
本届洛迦诺主要获奖名单见文末
深焦 x 徐冰/翟永明:这是对移动影像的反省和重新认识
采访 | 朱马查, Lycidas 发自洛迦诺
整理 | 朱马查, Lycidas
深焦:虽然新闻发布会时已经说过了,但我们从头讲起,能不能请您再讲述一下,怎么想到要做一个关于监控录像的项目的?
徐冰:最早是2013年,看电视的时候看到法制节目中有很多的监控画面。我当时看到这些监控画面给我很深的印象,很真实,给人一种很特殊的移动影像的魅力,这种魅力在监控画面里面特别强烈。我当时就想,谁能用这些画面做一个剧情长片,那这个电影一定是非常特殊的。
深焦:所以,从一开始您就知道,这个项目得是一个电影项目,因为毕竟您之前从未涉及过这个领域。
徐冰:对,首先想法就是做电影。我对这个还是挺敏感的,我首先意识到,这必须是一个长片,一个故事片,如果只是一个艺术家的视频艺术(video art),就没意思,因为类似的已经很多了,真的也好,假的也好,即景也好,都不会有效的。而且你必须有一个故事,一个叙事,如果监控影像能够完成一个相对复杂的叙事,那他就说明了监控影像和我们今天的人的关系。
当然,我当时可能并没有想到和人类的关系这一层,我想的更多是这些监控影像和惯常的电影影像之间的张力。因为,监控影像对我有特殊的吸引力,那一定是和一般的电影影像是有区别,因为一般电影的影像可能已经让人没什么感觉了,因为他们的构图是非常程式化,就和我们画画的人摆放静物的程式化是一样的,前面一个罐子,旁边俩苹果,后面一个衬布斜着。这就是我们构图的训练,在摄影里也是一样的。那些东西和那些效果,暴力什么的,都是被制造出来的,你会觉得监控影像和这些东西是不同的。你要是用这些(监控影像)戏仿一个电影,把故事讲出来,那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是)对人类创造出来的移动影像是一个反省,对移动影像的本质的一个反省和重新认识。我觉得在电影的范畴,剧情片的范畴中,所有的影像都是假的,演出来的,造出来的,但是人类创造移动影像的时候,它的目的并不是创造这种假象,而是反映真实,把人类真实活动的再呈现。

《蜻蜓之眼》海报
深焦:所以这整个作品的出发点就是对电影这门艺术的戏仿。
徐冰:对,当时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主要还是从视觉感受上来想这个事情。这个想法就和我当初做《天书》的时候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有了这样一个想法,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够做成,但是是很值得去做的,是很有野心的想法。
最开始我就是托朋友帮我搞了一些监控录像的录影带,这个记录的是一个医院里的停车场。我看这个画面的时候,因为没有声音,我就试着看着这里面出现的人物自己编故事。编了故事以后我就认定这个想法一定是可行的,只要有足够的影像资料。概念是成立的。
我开始试图去写故事,但我没有接触过编剧这件事,我觉得在整个电影里,编剧可能是最难的,我当时试着写,但写出来其实是个流水账,所以才请了张憾依和翟永明来写,因为编剧其实是一个很技术很特殊的东西。
一开始比较明确的是写一个整容的故事,主要是因为要解释这个故事中的主角没有固定的形象的问题,整容可以不断的改变样子,好像可以弥补这个缺失。主要还是为了解决技术难度的问题。
深焦: 所以与大多数电影背道而驰,这里叙事是为影像而服务、而调整的?
徐冰:这个故事的起点是为了使用这种特殊的影像而设计的,当然实际上“整容”这个起点其实和监控影像这个主题也是相关的。我们看到的是不是真实的,外表和实质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还有,身份的问题。真实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她整容了,这个人到底还是不是这个人?这些问题都和我们的主题有关系。
当然你的问题其实是素材和故事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来来回回的过程,他们写,写完了之后有的情节挺有意思,但没这么多材料……
翟永明:比如我们写了监狱里的戏,以为监狱里应该有很多监控的录像,结果根本就找不到,所以整个监狱的戏都删掉了,直接出个字幕“三年后”……
徐冰:还有时候是写了,但是画面里口型对不上,又只能重新写,或是用旁白的方式。

徐冰和翟永明,剪辑师马修,张文超在洛迦诺电影节
深焦:这样的材料对于叙事的限制是很大的。
徐冰:是的。有的时候你需要很长一段对话,但是这个场景就这么长,没法说更多,所以又需要根据它来来回调整对白。反正总的来说,这个电影就是各种因素都是相互来补充和调节,来支撑来解释,来来回回在一个夹缝中(完成)。很多人都说不可能,包括搞电影的人,但我相信,一定是有一个缝隙是可以走过去的,而你需要把所有的可能性全用上,一点都不浪费。就比如说,一个故事可以说到一百分,但由于你没有工作到位,说到六十分,或者再努力一点,说到了八十分,但你还是浪费了二十分。因为它只是一个缝隙,这个缝隙,你要是走通了就是走通了,走不通就是走不通。比如声音怎么处理,图像的碎片之间怎么衔接,当你做得非常到位,而没有浪费任何的可能性的时候,你就可以尽可能地达到他应该到的分数。
深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听说这个电影的故事经历了非常多的版本?
徐冰:是的。

《蜻蜓之眼》剧照
深焦:那么这个项目总共做了有多久?
徐冰:2013年就有了这个主意,但是后来就停下来了,比较正式开始写这个故事是在两年以前,就是我忽然发现偶然间发现网络上有很多监控录像出现,而这些监控画面(在网络)的出现,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素材)我们越挖掘越多,最后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得多,比如我们以为寺院不太可能有摄像头,结果后来发现寺院里的素材太丰富了。后来我们分析为什么,因为现在寺院都市场化了,而这些影像都是在做广告,再一个,寺院直播这些人念经布道都是在弘扬佛法呢,就是他们自己都把这些传到网上。
深焦:我知道翟永明老师是一位影迷,那您之前对电影关注得多吗?
徐冰:我看得不多,但是我了解几乎所有的,世界范围内的艺术家范畴的影像作品。
深焦:那在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您对于自己在电影手法上能带来的变化或是甚至说颠覆抱有怎样的想法,除了我们之前说到的这种对于电影艺术本身的戏仿?
徐冰:我这人工作,做什么东西有一个最核心的判断,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值得做。因为我其实觉得大多数艺术作品不值得做。我一旦判断一个东西值得做,我就会全力以赴地做,而且我其实有点喜欢有点挑战性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值不值得做,是不是有人做过,如果别人做过,就像别人说过的话一样,是没有必要再说的。我相信这种手法做电影是没有人做过的,事实上,早两年也是做不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一直在搜寻,做了很多研究,而且我们的朋友知道我们在做,也随时向我们提示,哪些电影是和监控有关系的,还提到了一个电影叫Look(注:《众生相》,2007),他是把摄像头放在公共摄像头的边上,但是他最后故事进行不下去了,还得让演员到摄像头下面去演。

《蜻蜓之眼》在洛迦诺电影节新闻发布会
深焦:对,因为导演使用监控镜头视角的并不少,而全部使用档案影像制作的纪录片也不少,但是您是全部使用监控影像来讲述一个完全不同的虚构故事的。
徐冰:确实有很多朋友也跟我建议说,你可以怎么怎么样。但我觉得都不行,因为我觉得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极致,我要求这个电影所有的画面都必须是监控画面,都必须是真实发生的,而没有摄影师的痕迹,没有表演。比如说导演把摄影机放在监控镜头的边上,这其实已经是一个摄影师的存在了,因为他设定了一个角度。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一直在判断,到底什么是监控影像的界限。这个是很难的,可能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判断清楚,但我们只能是为我们的作品做一个界定。比如我们讨论了很久,行车记录仪究竟算不算监控录像,我觉得是算的,那么判断准则就是它本身的这个画面不是为了一个(电影)摄影的目的,它是没有意识的,在我们这个电影里所有画面的原始意图都不是为了这个电影的。
翟永明:其实因为行车记录仪它也是一直拍摄,在等待事件的发生,这一点和监控仪其实是一样的。
深焦:但这里也有网络上的网红主播的直播影像,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去界定“监控”的边界,因为这些影像它还是有表演性的,这些主播有去选择镜头摆放的角度,在镜头面前呈现的样子等等。

《蜻蜓之眼》剧照
徐冰:(其实要看)这个东西本质上和我们电影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种监控,因为这是他们的生活,这个记录的是他的真实的生活的状况。虽然这个好像和电视台主播的画面也是没法严格区分的,因为那也是主播的生活的真实状况,但是电视台影像的目标就是电视机前的观众。而这个网红他的目的不是我们电影的观众,他不是为了我们的电影在表演的。
这是他们(网红)的真实生活的一部分,你看有很多就在直播吃饭睡觉什么的,只不过这个网红在镜头面前这部分生活刚好就是表演,他们好像在模仿电视台的主播,但本质上,他们等于是主动被监控,主动把自己的生活长时间放在监控镜头下。还有一个头疼判断的是那些“live show”,还有戴在头上的Go pro呢?你戴在头上,可以有意识的通过行走的方向控制要拍摄的范围,但也可以是无意识录下来的……我们其实什么都想过了。
总的来说,今天的很多现象已经超出了我们旧有的概念范畴的,几乎任何事情,旧的概念都是无从判断的,就像我们对于“监控”的判断,最后就只能归于说,这个电影中,没有一帧画面是我们安排的。因为那个判断是今天的人类的知识和逻辑无法做到的,因为太多新的现象,变化太快了。人的思维已经跟不上了,很多东西人类是没有时间来反省和整理的。
深焦:片中涉及了非常多的话题,从整容到直播,社会上的暴力,性骚扰,还有寺庙的世俗化好像也是要体现传统的衰落,所以除了适应监控的影像,这个叙事也是有意识地要去做一个这样广泛的社会现实批判的吗?
翟永明:批判是肯定有的。比如我们写寺庙,肯定不可能再写成古代寺庙的样子,因为也不存在了,我们都不需要说话,这画面里真实发生的一看就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
现在这个社会它对包括整容、变性等等有一种不一样的影响,比如对女性的影响,对不同族群的影响。我作为编剧,我是不能完全认同社会上流行的很多观点的,比如觉得整容就是女性的虚荣,好像女孩儿就是为了虚荣和名利,但我觉得肯定不仅仅是这样的,而是涉及到这个社会对女性无形的压迫,我们想要表现女性在这个社会上受到的一些潜在的性别歧视。尤其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很注重外表的社会,什么都讲一个“颜值”,有很多人在生活和职场上都受到影响。你可以从那些广告,还有招聘广告看出当今社会上女性的地位,好像这种对于外表的要求在创造大家对于整容的需求,但是整容的风气流行起来,社会上又反过来批判女性爱慕虚荣。

《蜻蜓之眼》剧照
深焦:其实这个故事里,对整容这件事并没有什么批判的意味,某种程度上这甚至成为了故事主人公成全爱情的一种方式。
翟永明:对,我希望就是通过整容这件事,把女性的复杂性也表现出来。
深焦:感觉故事发展到这部分还蛮解构的。
翟永明:对,因为这部电影的材质,手法上的特殊性,我们的剧情上也应该有点特殊,不能完全俗套的结构和故事,也就不配这个题材和手法了。
深焦:其实这些都是现实中的影像,但放在这里面会显得特别的超现实,所以用这种事实影像来陪这种超现实的主题确实可能是比较贴切的。
徐冰:我们之前说到了很多个版本的故事,其实第一个定剪就是一个很写实,很自然主义的故事,太像很多中国导演拍的(电影),(就是)贾樟柯的思路。
翟永明:故事过于完整。因为一开始特别怕故事讲不下去……
徐冰:对,特别怕故事讲不下去,或者串不起来,所以我么的全部精力都在把故事讲出来,只要讲出来就是成功,结果居然是讲得太顺了,而且太写实了,因为画面都真实的,你故事太写实,那就顺撇儿了,就太腻,没意思,他的张力就没有了。当然这个阶段也有收获,就是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最担心的部分是不用担心的。可以说这种影像反而是解放了叙事。

徐冰在洛迦诺电影节
深焦:听说还有一个故事版本是是将剪辑师的剪辑过程也作为叙事的一部分放入片中?
翟永明:其实是我们之前设定蜻蜓和柯凡的故事其实是一个戏中戏,所以还有一个结构是工作室的人在寻找材料,但始终没有处理好,工作室的人又不能出镜,就只有声音出现,结果人家都不知道,还以为是警察在说话,反而变得很混乱,这个改了很多遍,最后还是放弃了。
深焦:这部片剪辑大概用了多久?
徐冰:一年,但不是一直在剪,有时两星期,有时一个月集中剪,然后停一段再重新开始,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往里补充素材。我们的工作室一个房间在剪辑,后面一个房间20台计算机一直在下载监控录像,场面可以说很科幻。我们有种感觉,这个的工作室好像跟全中国联系在一起,我们随时看到有意思的画面就会下载下来,看有没有可能补充进影片当中,能不能和故事发生关联。后来,我们的搜索开始变得比较有针对性,比如说需要一个山区路上有黑色的汽车在雨中驶过的画面,但找不到这样的镜头;这时候我们会先查天气预报,看到要下雨的合适路段就锁定那里的摄像头,等一晚上看是否有车经过;有一个镜头就是这样找到的。全中国的摄像头都是我们的摄影师。
深焦:影片里有很多表现灾难与暴力的画面,但大多数都发生在叙事以外,在主要的故事线当中反而这样的元素不是很多,这样安排是出于什么考虑?
徐冰:我们希望尽可能把这些素材用上,因为它们是监控影像里十分特殊的部分。监控影像绝大多数时间什么都不发生,安静得吓人,但即使没有事件发生,它也给看的人带来一种紧张感,这是影像本身的特殊魅力。但一旦有事情发生,画面瞬间又会变得很疯狂,这些瞬间记录下的是超出我们人类逻辑范畴的事件,这对我们的教育意义非常大。比如说,一个小孩被面包车轧过去,前轮过去的时候鼓起来,后轮过去又鼓起来,但之后这个小孩站起来跑了。我经常想这件事,这怎么可能呢?但事实就是这样。这只是一件事,你想整个人类社会和自然界,过去曾经发生过多么奇特的,超出我们认知的事情,但我们不能说它发生了,因为没有被记录下来。只有在监控影像广泛存在,技术发达的今天才能够保存下更多挑战着我们的知识范畴的画面。要是没有这样的记录,我说一个小孩被面包车轧过去还能站起来,你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但现在你却不得不相信。监控影像让我们从一个全景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

《蜻蜓之眼》剧照
深焦:为什么要把这些奇特的、描述灾难的画面用在片中?
徐冰:其实最终还是为了故事的叙述,故事讲的是非常古典的,脆弱的人类情感。所有人,不管什么时代都会拥有的一种情感,非常私密。这些镜头都是为了衬托这种情感的 表述。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法判断、无法把握、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场中。我们工作团队的人出门都特别小心,因为处理素材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里大量看到了真实世界的样子,由此产生出强烈的紧张感和无从把握感,我们想把这种感觉在片中体现出来。
深焦: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集中展现这种天灾或者社会上的暴力,可能对于观众来说也比较残酷,而监控镜头本身也非常冷静,中立,可以说对拍摄对象漠不关心。
徐冰:它确实非常客观,无论发生什么都在那里。

本片编剧、诗人翟永明在洛迦诺电影节
深焦:片中还出现很多由机器念的诗,是翟老师的创作吗?
翟永明:是的。开始并没有打算写诗,本来只是想写电脑搜索过程,模拟机器分辨男人、女人、尼姑、居士等等人物时使用的词语,但后来写的时候处理得比较像诗。另外,也并不是每段都这样,刚开始的一段就是各种词语的排列,到第二段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像诗,但还是更偏向机器搜索的行为。第三段的时候,我开始感觉电影其他部分都表现了残酷的场面或者是激进的情感,所以我希望加入比较自然的东西。正好剧情到了柯凡进监狱的一段,监狱镜头比较难找,那么如何表现这三年的时间?所以我想到可以用春夏秋冬的季节交替,后来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段,配合的画面非常具有美感。
深焦:电影其他部分节奏都很紧张,但到了这里镜头一下就变得很平和。
翟永明:对,我感觉电影的四个部分非常像中国古典文学讲究的起承转合,到了这里是一个“转”,所以我们也就自然过渡到用比较诗意和自然的表现形式来讲述时间流逝,所以第三段机器画外音形式上就非常接近诗歌了;第四段谈到主题:“到底我是谁?”这个问题就更加如此。在我自己看来这部分的写作可能算是介于诗和非诗之间。同时也有点用它作为结构,用于分段的意思。
徐冰:我们后来发现这个很像印度电影里,过一段就唱一段歌,感觉上作用是类似的。(笑)这里面有这样一种考虑,比如最开始是很简洁的“男人”“女人”这样的词语,这种表述方式可以看作电脑的某种能力,构成和中国的诗词和日本俳句都很像,都是一种词语的堆叠。往后电脑的智能仿佛也在进步,电影的另外一个层次是在进展中的,整个电影使用的素材也是在进展中的。就像我的《地书》,多少年以前根本没法写出这本书,后来国际化程度提高,各种通用符号越来越多,emoji越来越丰富才能写出来。

徐冰创作的《地书》
这部电影也是,这里面最早的录像是1999年的,最新的是2017年。这个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监控技术的变化。早期监控画面是黑白的,后来有了颜色,清晰度提高,还有了声音;再后来变得越来越智能,能够自己跟踪识别和远近推拉。片中最后一个镜头拍到很多摄像头,从一边到另一边的镜头的追踪移动完全是摄像头内置的人工智能决定的。我有点担心别人会觉得是我们做了处理,但其实这个镜头并没有做任何剪辑,它自觉的移动配上肖玛唱的主题曲,效果非常好。
绝大多数镜头我们都尽可能保持其原始性。比如在表现寺庙的段落,彩色画面一下变成黑白,其实那是一个夜视镜头。监控录像在到了一定的暗度时,会自动切换成红外线的摄像,咔嗒一声是镜头自己调整的声音,不是我们后期接上的。

《蜻蜓之眼》剧照
深焦:关于片中出现的“地磁录像”,我们之前自己的讨论中觉得简直可以把它视作一种广义的监控,因为在合适的气候环境条件下能够重现历史现场。能谈谈为什么选取这个意象吗?
徐冰:这是一个传说,还没有被证实,但也不能说这种可能性不存在,因为人类的认识有限。这个安排是为了让我们更深刻地去反思监控,里面有一层含义是在探索监控的局限性和不真实性。尽管我们用的画面都是真实发生的,但这就是真实吗?其实不是。从更大范畴内来看,人类现在非常依赖监控,可是实际上我认为监控的画面和真实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距离。可能你从画面中看到的东西并不是你所理解的那样。我一直在想一件事,不知道谁能够把今天的监控影像都留存下来?我们这样设想,把望京一个月的监控影像全部储存下来,留给一百年后的人,那到时候他们如何认识今天的望京?那和我们为一百年后的人叙述的望京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后来发现监控影像可以改变我们的历史观,就像我常说的,要是当年鲁迅在上海的格子间有监控录像,那我们如今对鲁迅的判断和认识肯定不一样。但监控录像里的就是真实的鲁迅吗?显然也不是。它只是真实的素材,而不是真实的历史。可惜现在的监控影像在一定时间后都会自动删除,想储存时间长只能牺牲清晰度。
翟永明:但是现在存储技术和压缩技术都在飞速发展,所以在未来实现大量存储监控影像还是很有可能的。
深焦: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暗喻?
徐冰:没错。其实这里的一个暗喻是,也许地磁已经记录下来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不能说这是不可能的,毕竟现在科幻故事一个个被证实。而地球的确存在磁场,唯一问题是它是不是能够有记录的功能,这是非常神秘的。但回头看监控,即使人类花费大量智力和金钱发明了这种手段,但它所能实现的东西依然是有限的。
深焦DeepFocus前方影评:
完全以真实影像剪成虚构故事,这一超脱传统的创作形式是《蜻蜓之眼》对电影可能性的一次极具野心的探索。监控画面以全知的、“上帝视角”般的姿态,无差别而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每一个人,每一种生活的面貌。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现在,去中心化思想同样体现在媒介语言的革新上,使用无处不在的监控作为素材,本身便是打破单一视点,寻求多维度阐述历史的实践,与当下信息时代 “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带来的“科技——人类”关系的探讨不谋而合。
影片安排的叙事主线并不复杂,表层故事之外的一系列深层思考与诘问却颇为耐人寻味。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到底在何处?监控画面中出现了大量不可思议的现象,而近乎都市传说的“地磁影像”也是片中的重要象征:在深不可测的,以千年度量的世界面前,人类个体(乃至整代人)的认知局限暴露无遗。当下中国社会本身的种种戏剧性也无一例外呈现在监控之中,为故事蒙上了一层超现实色彩。《蜻蜓之眼》承载的丰富内涵并不止于此:女性承受的社会压力,“整容”带来的身份失落与倒错,无处不在的暴力、性骚扰、歧视…… 触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开放式结局与大量留白也让观众有了自己解读与思考的空间。
另一个隐含主题是改变,各个层面上的改变既是事件背景又是情节发展的推手,蜻蜓的出走与“回归”皆因种种改变驱使,通过师父之口我们得知这段经历其实只不过几年时间,但精心设计的转场镜头——无论是时光流逝季节变迁,社会百态的匆匆一瞥,还是猝不及防的灾难巨变——它们构筑起的极具沉浸感与洪荒感的视听空间,都让观者产生了一梦百年的不真实感。(Lycidas)
现如今的电影小时代,看得到庞然大物般的野心之作便已是可以击节的大快之事,而它仿佛在雨天穿越时间中一个逼仄的小巷,走到我们面前来,有其不可避免的捉襟见肘之处,你可以一眼看见它的一路的限制和磨损,但是它似乎又毫不在乎,仿佛它的到来反而是为了向我们展示这一路遇到的限制,彰示甚至是尖声提醒着我们这些限制的存在。
如此的一部所谓“高概念”的电影,承接着徐冰以前的艺术作品的一种“天书”般的不可进入性,又似乎一种微妙的反讽,很难用既定的电影规则、电影手法去衡量,而当你以为看见的是熟悉而古老的形式时,试图进入其中之意,获悉其全部意图却是不可能的。对电影的思考并非其兴趣所在,而是相反地用电影来思考其他的一切,是站在电影之外的一双监控之眼记录下这门艺术的轮廓与边界。
叙事也好空镜也好,所有片段在它们与这部电影的关系之外,还永远烙着另一层的涵义,另一重的生活,指向的都是无限的互联网浩瀚信息之海,指向一些模糊、无名、潜意识、集体的痛楚,指向一些“此刻谁在世上无端走向我”的莫名的沉重时刻,带来的是窒息般的惊惧与沉没感,同时又有一个大时代切肤的激烈快速的兴奋。
而同时,不管如何的“高概念”,它并不走入孤绝,它使用一个人人可与之联结的简单、传统甚至略有浅白的故事作为表面,就如其“地书”中的emoji叙事,用普世的语言与年轻人们的浪潮最前沿沟通,它是一个艺术家处理自身与所处的时代关系的苦心孤诣。(朱马查)
第70届洛迦诺电影节主要官方奖项名单
国际竞赛单元(Concorso internazionale)
金豹奖 Golden Leopard
王兵《方绣英》
评审团特别奖 Special Jury Prize
马可·杜特拉 / 朱莉安娜·罗夏斯《礼貌》
最佳导演 Best Direction
F. J. Ossang《九指神通》
最佳女演员 Best Actress
伊莎贝尔·于佩尔《海德女士》
最佳男演员 Best Actor
艾略特·克罗西特·霍弗《凛冬兄弟》
当代影人单元(Concorso Cineasti del presente)
当代影人-金豹奖
Illian Metev《3/4》
当代影人-评审团特别奖
Valerie Massadian《Milla》
最佳新导演 Best Emerging Director
金泰涣《初行》
特别提及 Special Mention
Pedro Cabeleira《可恶的夏天》
最佳处女作 Best First Festure
Ana Urushadze《可怕的妈妈》
短片国际竞赛单元
金豹奖(即最佳国际短片)
Cristina Hanes《Antonio E Catarina》
银豹奖
Miki Polonski《Shmama》

王兵获金豹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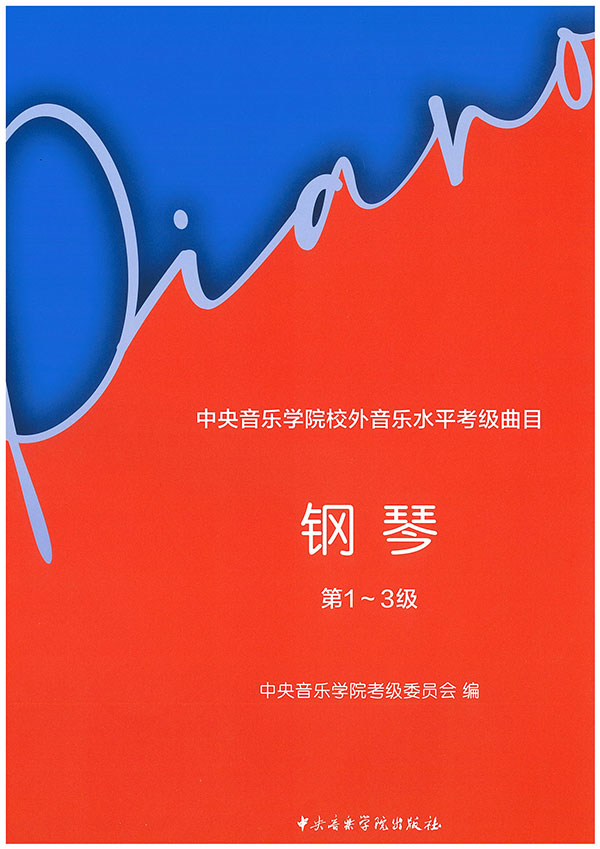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