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安全的是拿起画笔,它和时代有点距离”艺术家赵半狄的“归来

赵半狄电影《让熊猫飞》在豆瓣上得分只有2.4。(受访者供图/图)
这个时代,辨别艺术的含量其实非常困难,太难了,不仅仅是公众难,艺术创作者都难。
布置个展时,赵半狄看到了自己1987年的画作《涂口红的女孩》。画中气氛静谧,蓝衣女孩举着小镜子涂口红,里屋床上似乎躺着一个男人,正专心看报。2015年中国嘉德秋拍,《涂口红的女孩》以1380万元成交,这幅油画他已30年未见过。
大约30年的创作历程中,赵半狄转了个大弯。他先因“现实主义”油画著称,1991年底结识荷兰学者、策展人和收藏家戴汉志(Hans van Dijk)后,对西方艺术现状了解加深,不久即赴德国参展。
在戴汉志等人的“怂恿”下,赵半狄自1996年起创作以熊猫为主题的作品。2007年,他在北京举行“熊猫时装秀”,为二奶、性从业者、贪官、网红等社会角色设计了“熊猫时装”。
“熊猫时装秀”被动植物保护专家赵志龙形容为“恶搞”,后来有报道称,成都准备起草相关法律条例,禁止类似行为。
“一个人做出一件艺术作品,另一些人觉得侮辱了什么,这涉及多少层面?”赵半狄这样向记者记者发问。但在“熊猫时装秀”一年后,2008年6月中旬,赵半狄也公开抵制了即将上映的电影《功夫熊猫》,声言“不容许好莱坞在劫后余生的中国捞金”。他认为,“5·12”汶川地震后不久,上映美国娱乐电影并不妥当。最终,这部电影在成都推迟上映一天。
2013年,赵半狄导演了电影《让熊猫飞》。这是艺术慈善项目 “用创造力换一座孤老院”的副产品。孤老院顺利建成,电影在豆瓣仅得到2.4分。他因项目“累得一塌糊涂”,熊猫时代就此结束,其后几年,赵半狄陷入人生最迷茫的时光。
赵半狄后来重归油画。2016年,他举办了池边聚会“水下肖邦”,百余名宾客参加。一架钢琴置入池中,黑衣少女连续弹奏两小时肖邦名曲,腿始终浸在水里。赵半狄在池中用油彩和画布记下当时的灵感。
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提议下,赵半狄在尤伦斯举行了名为“赵半狄的中国Party”的回顾展,从2017年8月5日持续到10月22日。展品包括时装秀、电影、油画等重要作品。
那次“水下肖邦”的聚会视频在展览现场循环播放,文字说明写道:“风度翩翩的宾客沉醉在音乐和美酒间,一切很美妙,却令人不安。”
展厅门口陈设的小型装置作品《一个童话》创作于1994年,那时赵半狄放弃绘画不久。装置简单,一个小玻璃杯盛着鸡血,一根动物骨头插到血中,另外一头则固定着几张钞票叠成的纸花。作品标题与外观反差强烈,赵半狄认为,自己在其中平衡了优雅与残忍。“这个作品表达的并不是美,是对美的询问。”赵半狄说,它还询问了价值和方向感。

赵半狄装置作品《一个童话》。(受访者供图/图)
不知道干什么但知道躲什么
记者:你说最近三年“人生最迷茫,没有方向感”,具体怎样表现?
赵半狄:我觉得我是很有态度的一个人,虽然迷茫,不知道干什么,但知道躲什么。艺术界有主流意识,比如现在多媒体盛行,各种说法:AR、VR、浸入式的艺术……大家觉得好像先进的艺术,我一定得躲。其实我都做过,1998年悉尼双年展邀请我在悉尼港做巨大的户外霓红灯装置,我做了,想和悉尼歌剧院遥相呼应。我觉得要做一个诗一般的口号,“我的心在颤抖”。做完之后,我接到两个大展的邀请,放弃了。我觉得那不属于我。如果做的话,我可能还是一个重量级的霓虹灯艺术家。
这个时代,辨别艺术的含量其实非常困难,太难了,不仅仅是公众难,艺术创作者都难。我想到佩斯北京的展,浸入式的花朵,艺术家们都很努力,大家排队观展。对公众来说,什么是美,都很简单,自拍出来艳丽、光鲜、五彩缤纷的,可能那就是美。
G20在杭州的晚会,西湖做的声光电,多媒体和现实穿梭,我看到芭蕾时直接就走了。这是对西湖的浸入式演出,美丽的西湖,美丽的芭蕾,无法分辨。
我相信创作者本身真的要创作美,但非常艰难。所以我会躲,不会轻易干这件事。最安全的是拿起画笔,画笔和时代有点距离,它落后。我宁可创作看起来有点落后的作品,我绝对反对未来主义。
记者:你起初画油画,后来转向和熊猫有关的行为艺术,现在重新开始画油画,这是不是一个国际化继而寻找本土的过程?
赵半狄:我没有寻找本土,我寻找我自己。有些人认为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关注现实,但我永远不是现实主义者。我想建立自己的空间,那是对现实另一种角度的看法。我放下熊猫,画了一两张画,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画面是我脑子里已经有的。我在美院上学的时候,那三年的作品真的在写生。画里1980年代的好莱坞的挂历,我都不动,不是我布置的。
记者:你时常会动情地回忆学者戴汉志,如果他还在世,对当下的中国艺术界会有什么感觉?
赵半狄:凭我对他的理解,应该不会舒服,应该不高兴。戴汉志先生是我关于前卫艺术的启蒙老师,和一个怂恿者,敲边鼓。你干什么事,他说“我帮你”;他从来没说“接着画”,一句话没有,都是乐着说:“好呀,你尝试。”
是不是侮辱熊猫是多么艰难的讨论
记者:你曾提到,自己那些兼顾优雅和戏谑的作品,可能令很多人不习惯。不习惯的究竟是什么?
赵半狄:有人觉得我首先考虑社会效果,他们错了。效果到一定程度,我的作品甚至让一些善良的人不舒服,那不是有意识的,而是美的底线产生了压迫感。
世界是多层的。我要追求自己的世界。我尊重宗教,它在现实层面上开辟出另一层世界,然后就是艺术,有能力的艺术家应该开辟一个层面。所谓“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梦想”。现实主义告诉我只是一个世界,只有一种方式,但我觉得艺术是这世界的另一个维度。
我的熊猫时装十周年,是这个展览很大的动因。优雅、戏谑是我的本质,我认为两者将产生化学反应,这个空间开始膨胀,挤压别的空间。某一天早晨起来,新浪副总编辑侯小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赵先生,你看一下今天早晨新浪的新闻。”四川的熊猫专家抗议熊猫时装秀,认为我侮辱了熊猫,因为时装秀里涉及二奶、三陪小姐这些角色。他们和熊猫每天相处,心目中有熊猫的形象,这一刹那他无法忍受,我的空间挤压到他审美的、道德的部分了。这是善良的,爱熊猫的人,我最不想伤害这部分人的情感。
是不是侮辱熊猫,这是多么艰难的讨论。一个人做出一件艺术作品,另一些人觉得侮辱了什么,这涉及多少层面?我想建造自己的秩序、自己的世界时,想象力没有到专家那里,但专家是第一个站起来抗议的,紧接着引起成都有些方面的反应,要开始一个“禁止侮辱熊猫法”。我的第一反应,真以为我的职业生涯遇到了瓶颈,某种法律可能会限制它,但这个法律后来不了了之。艺术超出边界、挤压边界很有意思,这里没有善恶问题,有非常复杂的人类学的、艺术的、道德的种种问题。这段事情对我的艺术很重要,我因此考虑到艺术的边界问题:我做出了一定影响,我的审美挑衅了一些固有的东西。记者:相较自己因时装秀被批评,公开抵制电影《功夫熊猫》上映时,你的位置一样吗?
赵半狄:“5·12”地震,我是第一批支援者,飞到映秀,惨烈之极。整个灾区非常悲凉,那种悲凉是无声的,人们说话的声音都很小。
回到北京接受《新京报》采访。有一个话题是谈即将上映的《功夫熊猫》。那时我很敏感,知道所有的娱乐节目是暂停的。我从灾区来的,一片悲情,认为现在娱乐期还没到。他们说理解我的感觉。我说,理解我就停映或者推迟。好莱坞这么大一个公司,我希望他们有人文关怀,应该自己撤出,那是多妙的选择。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任何合同都可以重新考虑。梦工厂没有这么做,太让我失望了。我觉得我的支持者很少,都没法站队。

2007年,赵半狄在北京举办“熊猫时装秀”。图为时装秀上的“贪官”。(受访者供图/图)
我鼓励“炒作”自己
记者:你为什么认为,“所谓炒作,是穿越封锁线所需要碰出的火花”?
赵半狄:这句话不适用于《功夫熊猫》。我去灾区,出于人格完善的考虑。发生这么大的事,在北京坐不住。我回来后,觉得自己发怒了,要说出来。我以为会挺简单:他们做错了,我点出来,他们就心虚了。
记者:你对“炒作”的判断,适用于哪些事例?
赵半狄:每个人都有宣传自己的成分。我鼓励“炒作”自己,在法律的框架内,有问题吗?有些时候不是炒作,就像我的熊猫时装秀,你的世界在膨胀,别人受不了了。
我在放弃熊猫的一刹那,觉得整个沟通有很大的问题。之前我不觉得,我很膨胀,觉得应该一往直前。
记者:为什么放弃熊猫项目?
赵半狄:我觉得我的构思,电影推广,鼓动机制,媒体监督,各方面已经设置得够完美了,编织这个剧本已经很牛了,但累得一塌糊涂。
我看不到明天的东西,也不相信有任何英雄能改变,所以我做完这么一个小小的项目,热情也就完了。
记者:电影《让熊猫飞》豆瓣评分只有2.4,和疲惫有关系吗?
赵半狄:电影是我一个项目的副产品,不符合电影工业的要求,也没有必要符合。我没有电影梦。在屏幕上勾画,起承转合,我觉得没趣,不精彩。我是一个行为艺术家,相信一次性、偶发。你的心理自己揣摩最好,揣摩观众的心理干吗?
有人说:“你能不能做得深刻一点?”我完全拒绝这种说法,我不一定要承担那些风险。我碎片式的、可爱的创意,能在现实中改变一点点东西,我基本是用最后的能量“裹胁”很多资源(此处指艺术慈善项目“用创造力换一座孤老院”)。全国两万多青少年给我创造作品,多少老师进来了,因为我是熊猫艺术家。
我喜欢这个阵势,谁的表演精彩,我们就随时把他塑造成主角。270小时的素材,尽量按照电影工业组合。闲的时候,我在爱奇艺这些网站看我的电影,点击率也不是很低,加起来能有1000万,留言几千条。我自己经常笑得不得了,评价认为我最low的点,全是我最嗨的点。
- 上一篇:抽象艺术的觉醒:走近被美术史遮蔽的传奇女画家
- 下一篇:职业艺术家的迁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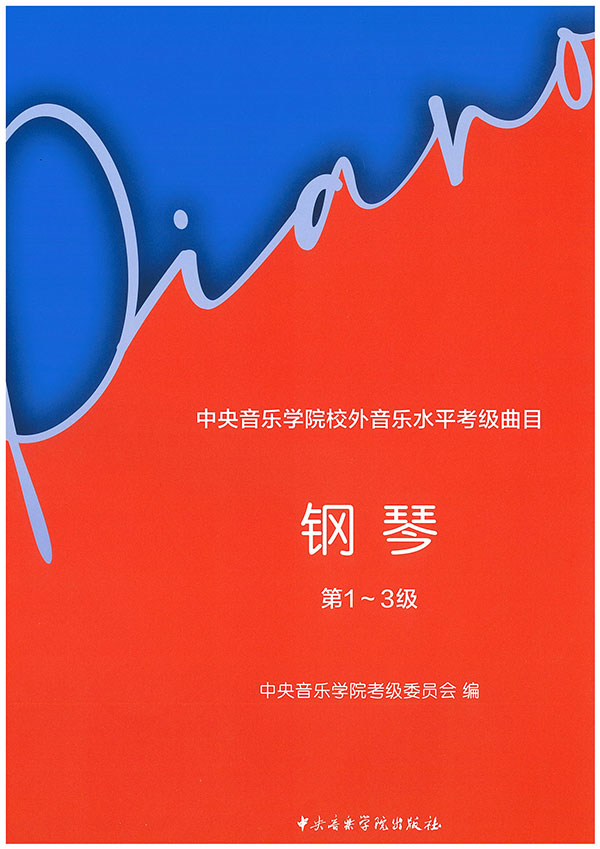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