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佴旻:由白菊花到楼兰古城

《太行的早晨》140x310cm 2012年 纸本设色
琢磨艺术创作的达成自然需要直觉和灵感的驱动,但未经深思的创作恐难以成就卓越乃至伟大。因此对杨佴旻艺术成就的研究和对其创作态势的关注,不能仅限于对其作品作赏读观感式的解析,我首先更有兴趣于艺术家的创作思想——它的缘起和走向。当问及个人创作阶段的演变,杨佴旻曾谈到,在他80年代末大学时代潜心版画创作时期,他一直未停止对水墨画的琢磨。与中国很多画家成长经历相似,杨佴旻由传统国画而叩开艺术之门,可以说画家的初心始于国画,但作为一个被不熄烈火般的熊熊创作雄心鼓动的艺术家,来自远方的呼唤让他很快就厌于抱规守旧:必须搞出点新的东西,一种契合于当下的活着的东西——正是这样的观念激发他的“琢磨”——当他说到对艺术的思考时,他强调“琢磨“一词,相对于思考这个词,琢磨似乎更能描述杨对中国现代绘画的实践性探索。观念必须体现于具体的技艺之中,并且通过最终的有效的文本得以验证,不可避免的,这要经历一些曲折,杨佴旻最终成了,通过持续的琢磨,而非空想和偶得。杨其实是个感性至极的艺术家,他曾自况是一个简单的艺术家。
事实上,杨佴旻从不依赖任何标新立异的观念成就其艺术。尽管中年的杨佴旻曾在南艺用五年的时间研习艺术理论并获博士头衔,但他显然不喜以任何理论或名头束缚自己的创作,历经对艺术乃至人生庞杂曲折的思考,他最终想要的乃是思想之盐,是琢磨的析出物,是形诸于本质之光彩的作品本身。因此,当杨说自己并不复杂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或许意味着,他坚拒用任何空心化的概念或浮华的词藻包装和配置艺术,他也不想培植那种观念的耐心,他用极单纯的艺术目光审视中国和世界艺术的历史和现实,他用很长的时间——琢磨,但是他的一切思考终将融入他的感性语系,一切的思考终化于他魔幻般的笔墨和色彩。
线条:对循规蹈矩的反抗
一个艺术家的风格是如何造就的?自然这非短期而成。但每一个风格艺术家皆发端于最初的体悟和思绪。虽未必一开始就注定了一切,但循规蹈矩的平庸者往往一开始就关闭了通向不凡的可能性,而一个卓越的属于明天的艺术家会很早寻求个性语言的确立并以此对抗任何既成的教育和范式的桎梏。比如,一些人会以为人只能通过房门出入,而窗口并不拥有此功能,但对于拥有一双翅膀者这个障碍并不存在:因为他完全可以从敞开的窗口飞出。当然,这只是一方面,现实总要比这复杂的多,没有窗口怎么办?对于隐形的窗口怎么办?可能性和方向在一开始未必是敞开和明朗的。作为杨佴旻创作历史的目击者之一,杨早期作品的粗厉特性给我留下强烈印象。青年时代的杨佴旻无论于创作和生活都不是一个安份角色,他着迷又很快不满足于自己的实验作品。他尝试不同的技术,而当他感到自己正滑向某种熟练时,即马上寻求另外的形式(而这也正是杨佴旻式的“琢磨”!)。当我们在一起谈论,我感觉得到他对未来和远方充满向往。事实上,如今的人们常谈论的“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于80年代即是杨佴旻选择的生活方式,他去大漠、戈壁、热带或海边,我相信是一种强烈的对远方的向往驱动他不断启程,这种诱惑强烈至此,以至于他甚至因为花光了路途的盘缠不得不逃票回家。自然,他的野心始终表现在他对创作的探索上,这其实是所有创造者的宿命:生命必须通过文本凝华。一切的意义必须回归作品,舍此人生的游历将被虚无的岁月吞噬。我曾去学院美术系的画室看他和他的同学们人体模特的素描作品,在一屋子的习作中,杨的作品以自己独特辨识度而吸住我的目光,显然他一开始就没有陷入追求“画得像”的技术精细的才艺满足感,笔意间难掩对物像的独特理解和解读,他要展现的不是描摹功底而是笔触的艺术表现力量。他用粗重线条突出人的身体的轮廓和律动,而这线条正是在模特身上看不到的被抽出的形式:对于艺术家来说,看不到的未必不存在。他的笔触夸张、充满力量和自信,并为下一幅创作埋下可能的改变的伏笔——而这正是展现一个艺术家无穷创造力的所在。
一个不伪装成业余的画家
没有难度的创作是不能成立的,人人皆可为的手艺不可称之为手艺,艺术创作更是如此。一个吊诡之处,在美术界,亦在诗歌界,在一定历史时期都曾出现甚至循环出现一种反智、反创作难度的思潮,使一些操弄者投机者以为有机可乘,亦使一些头脑不清者误以为那就是艺术,其结果是造成所谓艺术门槛的降低和艺术品味的败坏。另一方面,在当今时代,有一些人士,甚至以所谓业余性,边缘性为噱头,标以非主流的所谓先锋性面目,以博世人眼球并获取某种资本。此类人士的做派,不啻为终南捷径的现代版。在众声喧哗的现世,此种作法或许还真能一时“奏效”,或鱼目混珠而沽,或滥竽充数而鸣,但怕只怕终有水落石出之时,只剩下所谓“艺术家”而没有什么“艺术”了。一个清醒的创作者和观察者必须意识到艺术创作活动是一种诚实的艰辛的劳动,它必将持续性地挑战并消耗创作者的才华和激情。艺术是无限的,这并非意味着怎么都可以,艺术家的自由是无限的,但艺术家所能使用的自由却是有限的。条条大道通罗马,但做为一个孤身艺术家,他所能走的道路也只有一条。杨曾自述他小时候临摹芥子园画谱乃至完全背过,我以为正是这种不可绕过的笔墨功底为他将来对国画新技法的创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几乎是一种老生常谈,但艺术是“艺”而同时也是一种“术”,于躁动不安的当代,更特别需要一种严肃真诚的态度来对抗各种光怪陆离的观念对技术的鄙薄。当然,于学画阶段不同,杨佴旻在其慢长的创作生涯中,主要的致力于对技法的尝试和研究,在杨佴旻的一次作品研讨会上,受邀嘉宾诗人西川曾表示他对杨潜心研究中国当代水墨画这一姿态的关注,西川说:“我觉得在杨佴旻的画中,能够感觉到他不伪装成业余画家,他是以专业画家的姿态工作,表现出了一种研究的素质。这种研究不全是凭借他的才气——虽然在评价艺术工作者时我们经常会用到“才华横溢”之类的字眼,但这只是一方面——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艺术家的工作状态,这种工作状态实际上是一种研究状态。在杨佴旻的画中,不论是他的色彩还是构图,我都能看到一种研究性,这种研究性是那些伪装成业余画家的人所不具备的。”我以为此语是对杨佴旻及其作品极到位极有份量的判断和评价。
影响的焦虑以及遮蔽与还原
影响一个艺术家创作手法和风格的因素无处不在,这包括传统的也包括外来的,布罗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曾指出传统和大师的影响给艺术家带来的焦虑感,事实上这也是创作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杨佴旻对西方许多现代流派都有过研习并受到启发,但中国传统绘画对杨的影响则是最持久的同时也是渗透性的影响,如果没有这种影响,就无以理解杨对传统材料的以一贯之的钟情和志在必得的超越的雄心。从宋元文人画之兴起,以墨水主导绘画竟持续了几百年,中国画几百年的黯然失“色”历史让杨佴旻唏嘘感叹!事实上,从中国的更古老的文化根脉上原本是不乏色彩的,汉唐时丹青即是绘画之称谓,然自宋元以降的士大夫文化疏离了中国传统中本来既有的色彩元素,重水墨而轻色彩,数百年囿于所谓惟求神似,摈弃华艳,而营营自绕于所谓格高调雅的文人自娱的意绪之中,最终导致中国绘画艺术丧失了内在造血功能,其实这也暗合了一个古老文明由曾经的自信开放而渐至内向保守并走向衰微的过程。毋庸质疑,传统水墨画本身具有自己的思想情趣和审美价值,古中国的伟大画家们为中国也为世界创造了永恒经典的东方艺术,但经典属于永不复返的过去,旧有的语境已经消逝,今人复制过去的经典只据有向过去致敬和形式习练的意义,当今画家想要因袭传统的方式创造属于当代的伟大艺术无异于刻舟求剑。因此,对任何一个中国画家来说,虽则传统作品仍是值得研判和思索的对像,但什么是我们传统中仍然活着的东西以及哪些是需要摈弃的,传统的材料和形式在多大程度上应当传承或改变,以使当代艺术走入现代人的广阔精神世界?等等此类问题,却是摆在当代中国画家面前的一个严肃而迫切的问题。在杨佴旻看来,中国艺术的现代化来得有点太慢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有人抱着古人的审美眼光评判当代艺术,仍有人画着古代的画,抒发着所谓古代文人的情感,这岂止不真实,简直太荒谬了。一个头脑清醒的艺术家只要忠于自己眼见和内心实感,就不难发现我们所处的世界从来就是五彩缤纷的,从高山大川,危楼广厦,蓝天白云,溪流淙淙,到一花一木,一桌一椅,无一物不闪动着物像本然的色彩和光辉。万物本身的内在丰富性已经为目光敏锐的艺术家提供了表达不尽的可能性,如果一个艺术家对此视而不见,那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匮乏,而是艺术家自身的欠缺。杨佴旻一直寻求的正是意欲通过在表现技法上的突破,进而通过拯救失色的世界,而为现代的人们创造新的意境和语系,在他之前,林凤眠、吴冠中们所做的努力,都是在绘画创作实践中着力突破传统中重笔墨而轻色彩的痼疾,尝试通过引入色彩元素、借鉴油画表现技法等为中国画注入新的生命力,从力促中国画现代化上,杨佴旻是承前启后的佼佼者,于今他比先行者们走得更远,他已把中国画引入了充满未来的开阔地。纵观杨佴旻之画作,杨用其妙笔为我们还原了那个原本多彩的世界,当这个世界物什和草木以一种绚丽而怡然的形像呈现在我们眼前之时,我们才恍悟我们原来曾被一种陈腐的扭曲的审美观念钳制,而错失了对周边这个彩色世界的识读,遮蔽它的,是沉沉的历史和久久难以消散的内心的迷雾。
由白菊花到楼兰古城
杨佴旻曾多次谈及发生于三十多年前的八五新潮美术运动,于他本人来说,这也是其艺术个性和风格的探索期,充满了躁动、不安、跃跃欲试和不断闪现的新念头,他创作了大量的实验性作品,其中版画作品《乌里雅斯泰夏日的一天》获得了日本美术界的注意,被日本读卖新闻介绍为自鲁迅在中国倡导新兴版画以来最重要的版画家之一,但也就是这幅作品,由于其不合居主流地位的“高大上红亮”的官方标准而被布置于一个国家级美展的角落里,戏剧性的是,日本版画家山口雅三就是在角落里这幅画前伫足良久,并要求见见这位画家。而今回顾这一戏剧性细节,作品的时代及历史意义变得更加清晰:艺术必须重新审视我们所处的当代世界,关注人性,关注生命本体,才会还原它本来的意义,呈现它永在的本质。因此,作为一个自发的觉醒者,杨佴旻在创作的青春期即主动选择了一条求索之路。这是一条诱人的未知之路,也注定是一条艰辛之路。也就是那个时期,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传统画已走向末路必须寻求突破,但由于面临着传统审美趣味的巨大阻力,因而改变变得极为艰巨和复杂,可以说,与直接学习西方现代艺术不同,革新中国传统画是一个险途,是一道窄门。但是,年青艺术家们越来越意识到,传统表现方式所呈现的画境和意绪已与现代中国人的思想和情感形成隔膜,无法满足现代人的丰富的生命需求,也难怪此间,有人甚至怀疑中国画的工具和颜料本身,认为是这些硬件束缚了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而这也正是杨佴旻一边做着各种实践一边潜心琢磨的时期,90年代某一个月色皎洁的夜晚,作品白菊花在杨佴旻于保定的画室里完成了,当作品完成一刻,佴旻就知道这就是他想要的东西,得来全不费功夫,白菊花是他创作取得决定性突破的标志,但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个人风格的确立,更在于他打破了人们对中国画传统工具和材料的怀疑,在另一层面上,他对技法的拓展也为中国传统画连通现代打开了一个缺口——通过这个缺口看到的是另一番洞天,传统和现代的断层得以衔接,一种被压抑的潜能被释放,一种被人为禁行的路径如今发现可以走到未知的远方,一片世代只播种古老种属作物的土地,如今抽出现代的新植株。作为一个距佴旻不远的观察者,我目睹自其自完成白菊花创作至今的二十年,杨走在一条越走越开阔的新路之上,技艺由必然王国而进入自由王国,日趋丰富的题材展现着杨氏技法的巨大潜力,由小题材到大题材,由静物到人物,由具像到抽像,由现实手法到变形构成的尝试,我注意到杨似乎已到了想画什么都成的阶段,而这也正是我一直期待并相信杨佴旻能做成的事,画于近期的光的戈壁,楼兰古城等作品,则可显见其对色彩的理解已更加深刻,更趋本质,而这于仍然行走在路上的杨佴旻来说,其自然已收获今日之硕果,而其更大的意义当是在明天——当传说中的楼兰古城变成佴旻笔下的色彩的音符之时!
风格辨识和色彩魔力
对于创作来说,杨佴旻反对重复,厌恶烂熟。他一贯的思想,使他成为较早就具备创造意识的画家,他从来不自得于对物像的临摹,他目光如炬,捕捉的永远是事物在瞬间发出光辉的本质,他知道艺术无用,就像美的无用,但他却强调创作的有效,即美感的及物性,这大概就是他心目中艺术的意义。当杨还原世界的色彩之时,他还原的其实是有他的心加入构建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一个属性来自于对色彩的敏锐发现,但这个世界的构筑却借助了幻想的笔墨,他用笔触表达一种无声的旋律,用色彩抒写一行行静默之诗。因此,杨的色彩学似乎是攸关世界本质的唱辞,此本质并非定义而是激活,每件作品都是一个重新被发现的自我的本质在唱歌。
如果杨的作品给你的感觉是养眼,那你就被杨的美学风格击中第一个感触点。太舒服了,那样的一束玫瑰花你想拥有一束摆在窗前,那样的沙发你忍不住想去坐一坐,那样的果子你忍不住要去数一数它一共多少颗,尝一尝它肯定是甘甜的,那篱笆,那小园,那淙淙流水,触手可及,有时仿佛记忆,虽逝去但依然清晰,有时仿佛现实,只是因为某种错失,而将它忽略,而杨则用画笔把这些呈现于前,告诉你关于美的治愈性和它与你心灵的亲缘关系,一切迫近的曾被你和岁月白白的忽略,而如今一切遥远的似乎并不那么遥远。他用线条和色块解释物象,充满单纯而澄澈的概括力,你甚至来不及感叹我怎么没有发现,你心中块垒就为其所消融了,你沉浸于河流仿佛是水,你徜徉于中天又似乎是云。一个奇异的感受是,凡观其画中物者,会被赋予一种拥有感,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馈赠——一种慷慨的美的布施。
一切皆源于色彩的魔力,色彩的变化本无有穷尽,更何况那如风中天际白云般自由无碍的心——你应该好好观读一下佴旻笔下的蓝天白云,那简单之纯美美到无物之境!但中国古文人笔下是什么呢?写意的天空,被暗示的天空,被清高衬托的天空,对应着一颗无趣的宦海失意的心!难道用留白就表明了天空的存在吗?天空并不那么空!你见过有哪幅传统的水墨画这么耐心的描摹天空?它竟对蓝天白云这种无限寥廓的真实的美视而不见。油画自然很能表现天空丰富的色彩和层次,但可惜油画颜料却很难实现色彩和画布的交融,无论如何,它没有色墨与宣纸这种渗透互融的温润之德!极纯之蓝!极洁之白!被遮蔽的天空被眼睛再次发现,瞧,通过如此的蓝天白云,我们把天空的归还了天空,亦归还了人的心灵。而天空亦把它的无尽意回馈给我们,杨通过无痕的技艺,我们看到了画家至纯而喜乐的心。所谓,墨分五彩一说,是中国绘画传统理论中,对追求并相信技术的一个重要论说,但是,对于今天诸如杨佴旻等水墨艺术家,如果一墨分五彩,五彩又分几彩呢?有多少种红?多少种蓝?多少种紫?古人曾带着镣铐跳黑白之舞,而在五彩墨色中意欲穷极表现而至自由,这是历史的幽暗,旷古的寂寥!而今日之艺术家又何其幸也!
获救之物:本质与诗意
谈论色彩我们能谈论几分成色?色墨不言,自呈无限底意。我注意到佴旻之蓝,神秘而蕴含柔情;我观佴旻之红,恣意而不滥情;我赏佴旻之紫,高贵而不倨傲;我睹佴旻之褐,神秘而寥廓无际。有时,杨偏爱用玫瑰红,画家有情,而玫瑰亦有意,他爱它,它就静静开在瓶中,绽放于窗前,那玫瑰又似乎在报答画者之爱,似乎画家是种下它,而不是画下它。有时我思睹那玫瑰,觉它充满诱惑,那自然是非肉欲的诱惑,那似乎是有一个神秘之人在另一个世界的窗口摆放的一个信物,它提醒看到它的人,可以到那画里的世界去。我看佴旻的太行山图,见他用大量的赭石色系表现太行,于我有限的美术识见,赭石在中国画色系中本常做配料色之用,但在杨这里使它恢复了色彩的本相,当他大胆的大面积晕染太行时,它的太行是彩色的,它的赭石之土石,是彩色之歌吟。他这次是用简约而诗意的纯色写下他幻想中太行形态和梦幻。我终于发现色墨于佴旻而言,实乃他借物言志的诗句了。因此诗画源这一古老说法,于佴旻这里重获了它崭新的意义。
什么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必须包含艺术家的态度。艺术不是对现实描摹照本宣科,不是画得很像而已。我见过一个名头不小的艺术家自夸他画爱因斯坦画得像,我不认为这值得炫耀。艺术家的创造必须有一种态度,一种目光,一种可传达的态度和可共享的目光。说艺术家通过作品教育世人是不妥的,但艺术的确具备启发之功能,让世人看到凡俗眼未见之相。因此此间艺术家素养和修为就至关重要了。这决定艺术家将唤起物性中什么样的本质。因为粗鄙的艺术败坏人心,而美好的艺术则给我们以慰藉和鼓舞。在杨看来,本质是一种高度浓缩的诉诸于直觉的艺术气象,它即包含趣味也包含对趣味的体悟。它是一种如此真切不可替代的东西,因此杨自有其对艺术好坏判断的决不妥协的标准。
一花一叶,一几一案,一盘一盏,佴旻好多作品取材于静默之物,但有心人所见,凡其下笔之物,皆新鲜且充满活性,懂他的自然会懂,佴旻所绘者岂是状物,实作诗也!其诗不弄玄虚,闪动的都是物自体的光辉,他把世人寻常所见,皆赋予一种崭新的陌生,提醒你对身边物重新识读——特别被你久久忽略的美!我以为从诗学的角度查看,佴旻笔下之“诗”,极肖里尔克所主张之“物诗”。须知,言之(下笔)无物将使我们落入虚无的可怕陷阱,凌空虚蹈,我们必将坠地粉碎。靠观念,靠语怪力乱神,中国当代艺术之路只能走入歧途。意识到我们自己将消失,所谓艺术家做为个体也终将消失,就必须为自己的艺术作品日后的孤存负责。不错,作为创造的艺术是孤立的,这也是艺术家的孤独原因,但也惟其如此,艺术必须依存于物,并循物之形迹求索物之本质的飞马,方有希望抵达远方的神之居所。所以,如里尔克这样思绪深沉之人,也要从物诗开始,并格物而致幽微悠远。当然,此间所述艺术家对物的依存并非指衣食住行之需,而是作为创造者表现对像的物之为物的某种本质诗意的东西,于大诗人里尔克如此,于所有艺术家面向物的唤醒无不是如此!所以,物是人之所处世界初始和构成,人本身亦为物,杨的笔下,人物亦是有物性的。须注意,他笔下之物,非素描之物,非油画之物,乃色墨之物,物之魔力在于本质,本质之力量在于发现,发现之力量在于表现,表现之力量在于技术,技术之力量在于琢磨。杨笔下之静物自有其生命之喜悦,脱逃于传统痼疾,焕发崭新之觉悟。我以为这是杨佴旻静物作品的大贡献所在。
仁远乎哉以及杨佴旻作品的东方性
我不只一次听杨佴旻表达对坚持东方所谓道统的反对,时常甚为激烈。但在西方的一此评论家眼里看来,杨佴旻的作品一定深受儒释道的影响。佴旻说,儒释道里有很好的东西,今天的我们需要汲取的是它里面好的东西。但,我们今天再来谈论儒释道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装扮成古人与世界对话吗?——对西方膜拜或者迷信传统都是文化上不自信的表现,或者说是一种隐藏的功利心,而这功利心,正是我们东方文化所反对的。过去是个参照物,而当下才更需我们直面,最紧要的,我们需要关注的永远是人性的东西,从人性出发,从现代出发,我们再来重新审视我们的道统,我们才会发现什么是我们传统中活的东西,然后复归现实才能找到与世界交流的平台。因此,其拒绝作品的符号化,是研究杨佴旻作品及其艺术思想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更因此,所谓杨佴旻作品的东方性,事实上更应从审美特征意义上作理解。从毛绒绒的色彩触摸感这一观感,我曾想起王小波曾在一篇文章中嘲笑朱熹关于仁的解释,他援引朱的话说如有人看到小鸡雏的绒毛产生的感觉即是仁。于王小波来说,这简直是胡扯。但是,王先生过于轻薄了朱氏仁说在文化上美学上的意义,我以为:对于朱氏之说,如果我们扬弃其道统上的虚妄钳制,不去把它意识形态化,那么这里这个仁就仍具有继续讨论的意义。我想说杨笔下的色彩常给我这样的感觉,毛茸茸的,如新生鸡雏般的感觉,唤起自己内在之温情和善意,比如它奇妙的安慰作用,它的唤醒,它的陪伴,它的宁静的光泽和安祥的力量,我以为这皆包含仁之奥义——仁之唤醒,中国之传统得以被以现代绘画语汇阐释,不是我们必须去被迫接受承当什么使命,而是,我们从来就是是其所是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亦有赖于我们自己去不断重新认识,不断发掘。仁远吗?我欲仁仁就至吗?未必。但仁在。一种古老的感觉应被重新判断和表达,不是为了标新而与西方对抗,而是延续传统中真正具有内在生命力的东西。而它这种生命力被唤醒,它影响的将是世界而非仅是中国。基于中国复杂历史及现实,也许仁的精神远未被招回,但即使在这未来看起来模糊的时代,在一个太多精英有理由批判当代的这个当代,杨却用一种从容的创造力带给世人至善的鼓舞、确信及希望。仁也许远,但通过艺术的时空隧道,似乎我们又可以先期抵达。
作为诗人的杨佴旻
当我收到佴旻寄给我的诗集时我一时感到惊讶,之前我只知道他近年偶尔写诗玩儿。但当我读过它们,我又觉得这一切非常自然。他用词语去触摸他的色彩语言未及之境,抒发他自己内心世界的另一精神向度,面对此我既能感到佴旻熟悉和陌生的两面,一个始终钟情并歌唱着绚丽的世界,另一个则神游八荒驰骋物外。究竟何谓自由?自由是自由和对自由的渴望。或者,换言之,自由永远不是一种现实,而是一种运动。自由是克服风阻乘风而行的翅膀。对于创作来说,终点即是局限,即是不自由,因此,创作不应有终点。因此我认为,中年的杨佴旻忽然迷恋上写诗其实正是其自由心性的表现,他对所有新的形式和艺术语言始终充满好奇和尝试的热情,而这某种程度上正是诗写的核心动力,他貌似在玩儿,他把他的诗通过手机分享给他在生活中或旅途中认识的男人女人们,但一年之后,他出了一本厚厚的诗集。作为诗人的他怎么来抒写他的故土太行山呢?他写下自己内心深处的印记:——河床上的槐树林/夏天里慵懒的小花犬/所有的印记/乳名里的门户下植根我藏匿的栖息之所,他写下他的幻想:在砂石间——牧羊的路上/白云深处有太行仙女走来——一身紫衣冠/她笑了——出乎意外的美丽”他打开自己的喉咙:“我歌唱——/我是歌手/山巅更多的焰火吐出她的咽喉/我拧开银杏树枝上的水龙门”。在佴旻的诗里我们看到那个充满瑰丽幻想的乘风飞翔的少年,这既是他艺术的起点也是归宿。
继往开来者:贡献和可能性
抛开技法谈艺术创作也是虚妄的。但佴旻的贡献重要首先不在于他创造了一种技法,也不在于对色墨水纸本性的了然于心的谙熟,我以为他的重要性,一开始并且始终是一种紧扣现实并且永远求新求变的观念,他不只一次表现他对经典的态度,他丝毫没有贬斥经典之伟大的意思,如他对齐白石的尊崇是始终如一的,但是他更强调的是,艺术家的当代意识,就他的理解,所谓的现代化,并不是向西方看齐,而是以现代人之眼,观照当代之中国,当代之世界,从这个角度看,他对西方作品的研摹是试图了解另一个参照系下对事物的表现方式,这就是其作品以莫奈为蓝本的静物作品的意义,他没有重复,当同样的题材出现时,中国的当代艺术家要试着用我们的语言说出,相同吗?当然不,我的美学气息是你所不可替代的。不同吗?有一种对物本质的了解,一种相通的东西溶于其中,观者无论东西自然有一种无言的默契。另一方面,艺术不仅仅是一种表达,艺术也应是一种对话,艺术家通过艺术作品与观者灵魂的对话,而也正是通过对今者对话的实现,通过对现代人精神世界的艺术表现,必将为后世创造经典。佴旻的创作秉持这样一样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本身首先是对他自身的挑战,因为他必须否定自己既得的东西,作为一个中国画家他得于传统,而今后他则必须发现一种全新的语言,所谓必须的指令来自于自己的内心,一种内在促逼,庆幸的,然而又不是必然的是,他成了。必须注意到,佴旻不主要是一个做概念的艺术家,概念的玩家也许更容易看起来更新锐更符合某些人对现代艺术的期待,但是他的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笔者本人亦对这种虚无主义充满警惕,对艺术来说,态度永远是态度,观念永远是观念,艺术文本必须由根本的东西支撑,它不能是消解了技术的,真的,美的,自欺欺人的东西,换言之,万变不离其宗,就算是艺术家的名号没有门槛儿,艺术也永远是有门槛的。从这个角度说,佴旻的贡献则是历史性的,他的贡献是及物的,他处理的题材越普通,甚至越小,他的价值就越耐人寻味,首要的问题不在于画什么,而在于有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发现了什么,又通过如何的手段使那被发现物的本质发出可见光。他籍此解放了被遮蔽的中国画色彩的物自性,同时展现了精湛的个人才能。
用色墨新境之类的词形容杨的作品似乎并不够。杨所创造的并非新境。如果有境的话,其境的特色也不在新。新是一种感觉层面上的语汇,新在哪里为什么新?杨的贡献在于去蔽,这既包括观念层面也包括技术层面,当一种固有的观念充斥并成为标准的时候,旧观念将成为暴政。暴政之下是被遮蔽的物性,是物本质的旋律和绚丽。去蔽也就是还原,还原自然不是对物像的描摹,而是对物本性的还原,是打开物的无限开放性!因此毋宁说,杨在创造出令人赞叹的具有高度个人识别度的画作同时,他其实正为后来者开出一条新路,这不是一条无中生有的一条路,而是做为一种可能的路(方向)他或许始终存在着,杨发现了他。在这条新路上,每个艺术家都可以创造各自其新。因此,在谈论杨佴旻作品个人风格的同时,必须充分注意杨佴旻作品的历史性意义:他使用完全是传统的用具材料呈现物象时,它一方面发掘出中国画材料的潜在能力,特别是色彩的表现潜力和特质,另一方面从技法上打碎了来自于或旧或新的陈词滥调,成功的开拓了新技法的可能性,可以说杨为中国水墨画业已打开一条通向缤纷的色彩之路,这条路通向拥有无限可能性的诱人未来。以此判断,杨佴旻实是中国画当之无愧的继往开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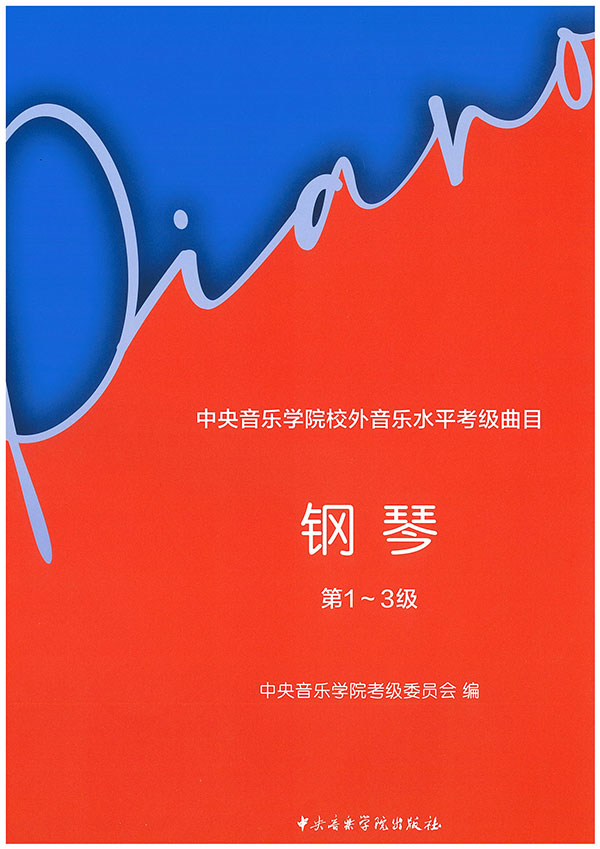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