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不是万能灵药 救不了你的坏故事
 |
| 《你若离开,我便浪迹天涯》摄影/本报记者 王晓溪 |
 |
| 《顶头锤》摄影/李晏 |
 |
| 《顶头锤》摄影/李晏 |
 |
| 《顶头锤》摄影/李晏 |
周健森
中国观众对于音乐剧的接受程度之低有目共睹,近年来情况似乎好转了些,但对具体剧目的态度还是有所区别。经典一些的海外引进作品,乐意捧场的人确实越来越多,但自己人的原创作品,讨喜的似乎并不多见。因此,上周三部本土原创音乐剧同时在京上演,这样的声势多少还是有些出人意料的。
此番上演的三部音乐剧,分别是韩红和田沁鑫联手打造的《阿尔兹记忆的爱情》,赵淼和樊冲共同创作的《你若离开,我便浪迹天涯》,以及香港话剧团的《顶头锤》。无论剧情还是表演形式,三部作品都可算作是与市场较为亲和的叙事音乐剧,或者说得更直白一些,它们都可划归到大众娱乐商品的范畴。
“大众娱乐商品”这个标签并非贬义,恰恰相反,要想让消费者心甘情愿地为娱乐埋单,其实很是考验创作者的能力。多年来,商业叙事作品的生产者们开发出了一整套完备的叙事模式和评价体系,艺术家们或许会对所谓“模式”嗤之以鼻,甚至谴责其绑架了创造力,但是对不起,若想在娱乐市场里谋生,这是起码的手艺。
将这三部音乐剧并置于商业叙事作品的评价体系之下来审视,票房并不算理想的《顶头锤》是唯一称得上质量合格的作品;演出结束后,人们讨论和点赞最多的,恰恰也是这部作品。如此说来,也许观众对于本土原创音乐剧的态度并不算苛刻,很多时候,人们仅仅是希望看到一个好故事。
《阿尔兹记忆的爱情》:一言不合就开唱
普通观众常以“一言不合就开唱”来表达对音乐剧的不解,《阿尔兹记忆的爱情》便可算是很让人不解的典型案例。这部作品有着韩国电影《我脑海中的橡皮擦》作为现成参考,但在舞台上呈现的却是一堆散碎的片段,无法串联成可以自圆其说的故事。
剧中有两条交错呈现的时间线,一条是女主人公行将失忆的残酷现实,一条是她七零八落的情感记忆,男主人公不断地被拖拽进回忆之中,而在现实的部分,尽管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人生困境,却看不到他们有任何突破困境的行动或信念,除了抱头喊着海誓山盟的口号,似乎也没有什么值得他们去努力的事情了。
观看这个缺乏推动力的故事,观众很像是陷进了一个泥沼旋涡,我们一边看着众多角色在舞台上像没头苍蝇一样毫无意义地原地打转,一边又惊愕于他们居然还可以饱含激情地掀起一曲高过一曲的亢奋音浪。不过这并不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剧中角色无需理由的爱与恨才真正叫人难以捉摸。
剧中女主的父亲一直反对女儿和男主的恋爱关系,但让人诧异的是,他仅仅和男主合唱了一首毫无叙事作用的煽情歌曲,便立即变成通情达理的知心准岳父。类似的还有一位专门与女主为敌的冷面女配角,在得知女主患上重病后马上登门道歉,改头换面成圣女闺蜜,只是我们不知道她究竟是因何获得了善意的感召。
创作者也许认为音乐是可以解释一切叙事缺陷的万能灵药,但这仅仅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观众调侃一些音乐剧作品时所说的“一言不合”,恰恰是因为其故事没能令人信服,也因此无法给予观众一个让情感释放的理由,由此产生了观看者和表演者之间无法认同的尴尬。这怨不得观众的理解力,这是创作者的失职。
《你若离开,我便浪迹天涯》:人物只抱怨不行动
相较于《阿尔兹记忆的爱情》,《你若离开,我便浪迹天涯》在叙事上表现得更为完整。生活片段快进式的序列拼接,使其规避了人物转变突兀的风险,甚至将戏剧性的人格自我冲突变成了一种有趣的风格。尽管这部作品给人的观感要更加愉悦,但是同样暴露出戏剧推动力不足的问题。
在这个描画三代人日常生活情境的故事中,创作者要么并未想清楚其主题究竟是什么,要么是想要表达的东西实在太多,使得全剧的主题一直不断游离和跑偏。从爱情婚姻到代沟问题,从关爱老人到亲情至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剧中人物莫名的焦虑,他们面前冲突成堆,却唯独没被赋予解决冲突的智慧。
该剧创作者在节目册中呼唤着“学会宽容、理解与爱”,但是我们疑心这三个普世的字眼被偷换成了“容忍、顺从与受”。面对伴侣的意见差异,子孙的叛逆反抗,以及女儿的粗暴管束,剧中主人公似乎始终没有主动去努力改善状况的打算,好像他们只要嘴上抱怨几句,一切就可以交给时间去自动修补了。
也许我们不该全盘否定剧中人物的努力,比如《阿尔兹记忆的爱情》中男主就策划了一场医院大逃亡,《你若离开,我便浪迹天涯》中的主角也经历了逃亡般的自由之旅。但这更像是创作者在剧情行将枯竭时的拼死自救,由于缺乏必要铺垫,强扭的高潮戏非但不能挽救全剧,反而更显出旱地拔葱般的鲁莽和尴尬。
鉴于《你若离开,我便浪迹天涯》大部分剧情发生在女主昏迷后的意识之中,我们本可期待创作者在结尾埋伏下神来之笔,来解决之前的问题。奇迹确实发生了——女主睁开双眼,一切矛盾自动烟消云散,Happy Ending团圆收场。这样的结局跟“一言不合就开唱”没有本质区别,不过是以泛滥的情感掩饰苍白的叙事。
《顶头锤》:受追捧因为用正确的方式讲对了故事
《顶头锤》比起上述两部作品的成功之处,并不在于其创作者有多么高明或独到的想法。这部作品没有如《阿尔兹记忆的爱情》那样的明星阵容,题材也不像《你若离开,我便浪迹天涯》那般更为内地观众熟悉,甚至其舞美呈现都有一种略显保守的传统质感,但在叙事上,这部作品用正确的方式讲对了故事。
将这个体育励志题材的故事套用在商业叙事的结构模式中去检验,就会发现其精准地吻合了教科书上的所有要求:足球少年的卑微身份和宏大志愿构成了主人公的内在冲突,踢进奥运的终极目标和家国沦陷的现实矛盾是构成其阻碍的外在冲突,不断升级的挑战,内外冲突的统一,少年成长的弧光……一切恰到好处。
有如此扎实的叙事结构打底,尽管这部作品中没有一个反面角色,但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每一个人物的故事轨迹,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以及必须共同面对的危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行为不仅符合各自的人物设定,而且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推动着剧情,这些角色是实在可信的,观众才会全神贯注地关注他们的命运。
比如剧中阿健这个角色,原本是无足轻重的配角,但是因为他小心翼翼藏匿了自己“在港日侨”的身份,便有了非同一般的分量。当他不得不在自己所爱的人面前坦白真相的时候,两人以一曲《樱之恋山茶》发出“只有憎恨另一个国家才是爱国的吗”这样的诘问,观众丝毫不会觉得此时的歌唱有多么矫情,因为我们理解他在命运抉择上的痛苦,并且和他站在了同一个层面的情感高度上。
一些文艺青年或许会批评《顶头锤》的标准化叙事陷入套路太深,没有创新的惊喜。客观地说,这部作品多少有些中庸的气质,放到百老汇或伦敦西区可能只是个及格作品,难成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爆款,但它确实成功抓住了观众。这个成功正源于其合格的叙事技巧,而在国内舞台上像这样及格的作品实在太少。
人物没血肉如塑料模特 时空抽离苦乐无关痛痒
为什么我们的一些音乐剧作品会在叙事层面漏洞百出?为什么这些作品所讲述的故事如此散碎且苍白?如果说这仅仅是叙事本身出了问题倒还不至于太过严重,毕竟技巧上的问题是最容易得到解决的。但是令我个人感到不安的是,在这些残破的碎片背后,故事讲述者或许暴露出了更为致命的创作倾向。
在此次上演的三部音乐剧中,《顶头锤》是唯一设置了具体时代和地域背景的作品,同时也是唯一有明确人物原型的作品。这个背景赋予了作品本身天然的历史感和独特的文化性,是故事外部冲突不可或缺的环境因素。而另外两部作品,创作者似乎都在有意无意地将背景模糊化,或者说抽象化。
《阿尔兹记忆的爱情》中的一些细节,如警察的装扮和说着东北方言的搞笑配角,让我们相信这个故事似乎应该发生在中国,但除此之外便无迹可寻。不仅如此,剧中人物的身份设定也几乎只是个符号而已,无论是爱上有妇之夫的富家女,还是怀揣职业梦想的草根男,似乎并没有什么分别,反正他们在舞台上只是负责扮靓耍帅,形象枯瘪造作得如同橱窗里的塑料模特。
《你若离开,我便浪迹天涯》号称是要“关注中国当下,关注中国普通家庭”,但是剧中人物的身上却丝毫没有具体历史年代的印迹,也没有反映任何当下百姓的普遍问题。他们更像是生活在海市蜃楼里的神仙眷侣,没人知道他们成长于哪朝哪代,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至于他们念念不忘的“蝴蝶岛”,简直就是个虚幻的乌托邦。
我不认可如此脱离现实的故事是所谓的符号化或寓言化的处理方式,剧中的那些人物与我所身处的现实环境无关,他们的生活是虚无缥缈的,他们不可能被填补进任何可以让我信服的细节真实,他们的喜怒哀乐也因此于我无关痛痒。我甚至不得不因此怀疑,那些创作者真的关心或了解现实生活本身吗?
我无法想象,那些疏离了真实生活的艺术家,对人们的日常处境陌生的创作者,没有费心去观察人们实际境遇、思考他们生存问题的精英们,如何去赚取观众的泪水或笑声。他们真的懂得生活拮据的草根青年为何会对一罐可乐斤斤计较吗?他们真的理解经历过“文革”年代的老年人如何看待情感关系吗?
如果创作者无意正视这个问题,那么我此前有关叙事技巧的讨论全都无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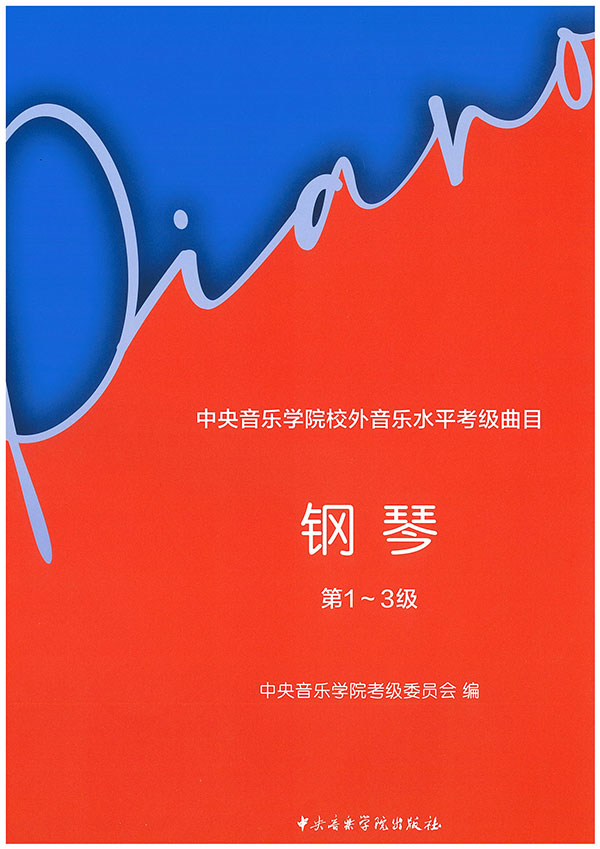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