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画家提香的遗产 受惠后辈大师

乌菲奇的雄庭(油画) 约1772年至1778年 约翰·佐法尼 英国温莎皇家收藏
彼得·汉弗利
早期传播确定其影响力
在提香去世后的400年里,无论在艺术家还是艺术爱好者心里,他一直是最受尊崇的欧洲画家之一。提香尚在世时,他的画作已经从威尼斯他的寄居地远行至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宫廷,以满足一群海外赞助人的巨大需求。提香去世后的几十年,这一流散过程急剧加速,因为17世纪的主要收藏家查理一世和他在英国的小圈子,罗马的教皇与主教,法国和奥地利的皇室,都彼此争夺提香的亲笔画作。约翰·佐法尼创作的《乌菲奇的雄庭》便充分展现了提香在17至18世纪皇室收藏中所拥有的优势地位。画中,一群英国绅士、鉴赏家欣赏并精挑细选古典雕塑典范之作,以及由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所搜集的早期绘画大师的作品。在前景的中央,很明显是提香那幅《乌比诺的维纳斯》,背后才是拉斐尔、柯勒乔和鲁本斯等大师的杰作。
此后,到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遍布欧美的公共美术馆的兴起,但凡有点雄心想展示最杰出的欧洲绘画收藏的美术馆,都会寻求至少获得一幅提香的作品。提香的作品一直饱受关注,吸引的对象不仅是历史学家和美学家这样的小圈子,还有更广泛的观众,两次致敬提香艺术的国际展览,1990年至1991年在威尼斯和华盛顿,2003年在伦敦和马德里,都举办得极其成功,显然证明了这一点。
提香能够成为西方艺术里最具影响力的画家之一,尤其要归功于其作品的早期传播。他是一位色彩大师,笔触极具表现力,这两点明显对后来者颇有启迪;不过,他为所有画作(祭坛画、肖像画、神话画,也许最突出的是女性裸体的表达)设计的构图,很快也对欧洲的形象塑造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艺术里不那么具体可见的方面,比如通过光影与风景调动诗意情绪的能力,或他对人性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的深切感受,也一直吸引并打动着他的艺术后继。最后,由瓦萨里《艺苑名人传》这样的早期传记,尤其是威尼斯人卡洛·里多尔菲更为详细的谄媚之作《提香传》(LifeofTitian,1648年)所传达出来的提香的人格形象,为后世几代画家提供了榜样,他们渴求也成为这样的艺术天才。
受惠后辈大师
要对提香的遗产做一个恰如其分的介绍,不得不提17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鲁本斯与提香其人其作的密切关系。作为宫廷画家,提香的艺术生涯为鲁本斯树立了典范,后者同样四处旅行,为国际统治阶层服务,同时也在其寄居地安特卫普保持着独立性。在旅行期间,鲁本斯不仅钻研了曼图亚、马德里和伦敦皇家收藏里提香的画作,也临摹了不少。跟提香一样,鲁本斯也接受了大范围各式各样的委托,在进行每一类主题的构图创作时,他都向这位先辈寻求指引,同时,也引入了自己的构图变化,扩展了表达的素材。比如,他讲述的狄安娜和卡丽斯托的故事,其构图和主题,很显然直接源自他1628年至1629年去马德里宫廷时对提香狄安娜组图的仔细揣摩,在色彩、光影及质地的丰富性和敏感性方面更是如此,而同时,他又将画作的预兆性与悲剧情绪,微妙地转变成肯定人生的乐观主义。
另外两位17世纪的绘画巨匠,凡·戴克和委拉斯凯兹,都强烈认同这位威尼斯前辈。他们分别是伦敦和马德里的宫廷画家,轻易就能欣赏到提香的作品,并且帮助他们的皇室主人多加收藏提香的作品。像鲁本斯一样,这两位画家学习提香的绘画技巧及构图模式,以此向前辈致敬,但同时也追求着不同的艺术目标。创作于约1647年至1651年的《镜前的维纳斯》只是其中一个例子,画中,委拉斯凯兹在提香式原型(就此例而言,是西班牙皇家收藏中斜倚维纳斯的各种表达)的基础上,巧妙且聪明地创作了自己的版本。凡·戴克那幅迷人的《洛梅里尼家族》(约1626年至1627年)也同样展示出画家如何充分吸取了提香的经验:如何为一组庄严的群像构图,以及既想画得像又想表现出理想的俊美,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潜在的冲突。
另一个同样受惠于提香的17世纪重要画家是伦勃朗,但他所受的影响要复杂得多。生活在重商城市阿姆斯特丹,伦勃朗学习提香原作的机会远不如鲁本斯、凡·戴克或委拉斯凯兹。而且,从伦勃朗的脾性来说,他也不想采用那类对提香来说如此自然而然的理想范式。不过,他有时也会在阿姆斯特丹的艺术市场里看到提香的画作,包括1640年左右进入艺术市场的《蓝袖男人》和几年之前的《弗洛拉》。前者为伦勃朗最杰出的自画像之一(现藏伦敦国家美术馆)提供了基础,后者似乎是伦勃朗妻子萨斯基亚肖像画的底蕴。尽管《萨斯基亚》的自然主义特征丝毫不逊于古典的理想美,但她脸庞及衣服上光影的飞洒、温暖的色域,以及伦勃朗绘画手法的变化多端,毫无疑问揭示出此画与提香对审美及人性的许多关注点是一致的。在伦勃朗17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后期作品中,他越来越关注颜色的物质属性以及表达的精神深度,这一点与提香晚年的走向相当类似。
在提香式的传统里作画
17世纪早期的这些艺术大家如此全面深入地吸取了提香的构图风格与范式,使得后几代的画家,尽管毫无疑问是在提香式的传统里作画,但也常常更直接地呼应他的这些后继。因此18世纪及19世纪早期的画家,比如华托和德拉克洛瓦借鉴委罗内塞和鲁本斯,戈雅借鉴委拉斯凯兹,雷诺兹借鉴伦勃朗、凡·戴克和鲁本斯。同样,提香在批评界和学术界的声名也一直与鲁本斯的名望紧密联系在一起。17世纪末,在法兰西学院内普桑派与鲁本斯派的争论中,提香自然被鲁本斯派列为例证。这一争论是16世纪素描——色彩之争的回归,一方支持线条、雕塑形式及理想的古典美,另一方则支持色彩、强调色彩的画法以及自然主义。与普桑派正统完全保持一致的,是雷诺兹的学院声明,其第11份《论札》(Discourse,1782年)声称,与拉斐尔相比,提香“脑海中没有任何关于美的一般概念,因此缺乏修正自己模特线条的能力”。不过,雷诺兹也没有被自己的信条所蒙蔽,继续用充满欣赏的温暖笔调提到提香:“不管是人、动物,甚至是静止的物,无论其外表如何死气沉沉,在这位天才画家的手里,都可以提升神性、传达感受、制造情绪……他画笔所及之处,不管如何天生平庸,日常所悉,都通过某种魔力,注入了庄严与意义。”
后来的“浪漫派”英国画家,更是尽情呼应提香。比如特纳,尽管他专攻风景画,着眼于提香艺术中之前被认为是次要的方面,但他被《欧罗巴的受辱》这样的画作所打动,画中那消逝的、几乎是虚幻的背景效果对他影响颇深。这在特纳1842年的一幅画作《坎普桑托》里十分明显,这是特纳描绘威尼斯风光的许多画作之一,其景色接近于提香十分熟悉的风景,当后者从比利·格兰德的房子北望他的家乡多罗米克山脉时,便可看到这一风光。
随着19世纪中期以来进步画家渐渐抛弃了文艺复兴现实主义及其学院派教条,对他们大部分人来说,提香更像是某位遥远的艺术先祖了。艺术家们仍然关注线条与形式在思想表达上的清晰性,或色彩在感官与情绪上的运用,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20世纪中期,只要想一想对立的皮特·蒙德里安和杰克逊·波洛克就可以了。但是,对绘画性的本能不再必然暗示着艺术家意识到或者欣赏提香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不过,对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的许多重要艺术家来说,提香的确仍然是他们灵感直接的、真正的来源。雷诺阿便承认说:“那个提香老头!他长得都像我,他一直在偷我的花招呢。”
一个十分出名甚至是臭名昭着的例子,那就是爱德华·马奈1863年的《奥林匹亚》。在处理一个在19世纪中期法国具有高度话题相关性的主题,即妓女主题时,马奈发现,通过以提香的《乌比诺的维纳斯》为构图基础,他可以为自己的画作更添一份庄重与冲击,他还是学生时曾在乌菲奇美术馆临摹过那幅作品。
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尽管越来越容易获得提香作品的彩色复制品,但之前不太为人所知的杰作的重新浮现,依然能对当代绘画实践造成冲击。在《工作空间》一着中,美国抽象画家弗兰克·斯特拉生动地描绘了自己在1983年“威尼斯天才”伦敦展中观赏《遭剥皮的玛尔叙阿斯》的体验。画作令人不安的残酷主题让斯特拉感受到情绪上的冲击力,同时,他也在绘画的空间张力及身体能量中发现了突破僵局之道——在大部分当代抽象艺术中,硬线条几何学已经走向了死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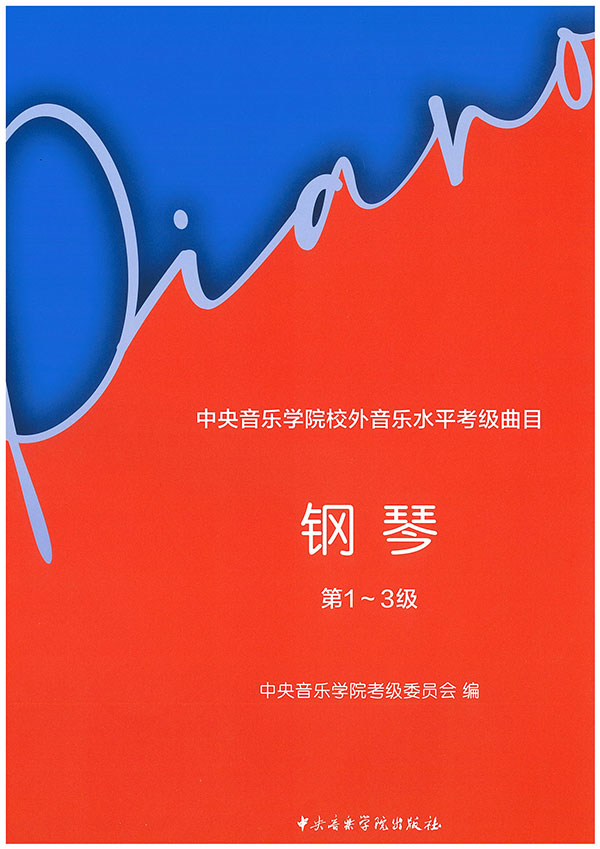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