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期的南画:受中国二流画家影响的日本文人画
江户时期(1603-1868)被誉为日本绘画的黄金年代,德川家康(1543-1616)在1603年于江户建立了幕府政权,幕府为巩固权力分封领地予诸侯(大名),诸侯的居城也成为商业与文化的重心,号称三都的江户、京都与大阪成为商品经济流通的枢纽,繁荣至今。政治安定、快速都市化以及国际间文化交流为该时期的重要特征,最为我们所熟知的是葛饰北斋(1760-1849)、歌川广重(1797-1858)等画家的系列版画作品对欧洲印象派创作的影响。不过在对外输出的影响之外,江户时期绘画亦承载了来自其他文化的影响,例如受中国文人画影响的“南画”(Nanga)。然而,江户时期“南画”这种反院体绘画而生的文人画潮流,究竟是文人士大夫的高雅创作,还是迎合了市民品味的商业作品?日本南画既是受中国文人画影响,南画家的图像来源又是什么?

梵高(右)临摹歌川广重作品《名所江户百景:大桥安宅遇雨》。
我们常常会关注江户美术中活跃、创新的一面,而忽略该时期主流美术界的背景氛围。整体而言,江户美术界仍十分重视传统院派体系,“团体”、“师承”、“层级”与“纪律”概念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个人”与“主观创新”。在这样的氛围下,加之德川幕府扶植儒家哲学与治国方略的研究,江户等地纷纷涌现出各类汉学学校,日本美术界兴起了一股文人画潮流,文人画家们希望摆脱院画的精雕细琢、浓艳设色,追求内心情感的表达并推崇“逸品”画风,这类文人画即被称作“南画”。简言之,南画家追求的是描绘“心中之画”以及进行纯粹艺术创作。

祇園南海《墨梅》。祇園南海(1674-1751)为第一代南画家,其《墨梅》一图中,梅树扭曲的枝干于画面中部猝然消失,似乎在用尽水墨时自然中止运笔。画家没有模仿自然世界梅树生长的状态,而是绘制其心中的梅树,也体现了文人习惯于洞悉画作外观之下深层意涵的特性。
南画并非指“南方人所画的画”或“描绘南方的画作”,而是指一种心态上的“南方状态”,即享受安逸生活、个人自由空间,投身于纯粹艺术创作的状态。“南方状态”是相对于“北方状态”而言,此概念来自中国画坛的南北对立,晚明文人画家董其昌的画论中即阐述了北方职业画家与南方文人画家之差异。董其昌在16世纪末受松江一地鉴赏圈影响,希望建构画史的普遍规律性,他在《论画琐言》中引进禅宗南北二派划分法作为追溯画史系脉的典范。相较于北方,南方独特的地理气候给予了文人更加闲适宽裕的生活条件,若北方代表官场、功名利禄、理性,南方即代表着归隐、悠闲与感性。不过日本的南画概念,并没有明确的地理、政治层面区分,南画这一概念在日本并不是指地理空间之“南”或社会阶层上的士人致仕。日本的文人士大夫并不像中国的退休文人有“庄园”可去,他们无法前往真正的南方安度晚年,故他们追求的南方性只是一体制内的南方心态,即一位文人可以在心理层面上白天工作,夜间以“南方状态”享受业余生活之乐。
不过,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南画的理想固然清高,南画家却面临着两个最为棘手的问题:金钱来源和图像来源问题。
金钱来源:“去商业性”与“商业性”共存
就金钱方面,任何艺术创作都离不开赞助者的支持。然而不似中国拥有悠久传统的文人画,日本并无文人画传统,江户时期国家大力赞助的仍为寺院的院派画家,那些世代相传的职业画家才是画坛主流。南画兴起的初衷虽为追求纯粹艺术与业余精神,南画家们起初也不屑于与职业画家一样出售自己的画作,他们认为将艺术创作与金钱挂勾庸俗不堪;然而绝大多数南画家却因经济窘迫不得不出售自己的作品,一些画家也看准时机利用文人画潮流大赚一笔。因此在审视南画时,其所兼具的“去商业性”与“商业性”需要被时刻铭记。
为了使画作获得更高的知名度以及商业潜在价值,南画家们有两个办法,其一,以传统屏风形式绘制文人题材画作;其二,刻意以文人理想以及“南方状态”为卖点吸引买者。就第一种方法而言,首先需要解释一下何谓“文人题材”。虽然名义上南画是绘制“心中之画”,而文人的“心中之画”当然不同于庸俗之人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岁寒三友、江山高隐才是符合文人品味的主题。为配合如此高洁的主题,“墨戏”成了文人画家最为看重技法。所谓“墨戏”,是一种“书法入画”技法,即运用书法的运笔方式进行绘画创作,唐代的吴道子是此技法的开山鼻祖。日本业余画家也继承了此品味,他们选择绘制单色水墨画,尽量避免使用鲜艳的颜色,这样一方面可以区别于职业画家,另一方面可藉由单色水墨画体现他们作为文人的自我节制。不过墨戏并非在江户时期才出现,中古画家即已开始大量使用“破墨”画法,例如室町时代相国寺僧人画家雪舟等杨(1420-1506)即是此种画法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破墨山水图》以寥寥数笔点染山水,并不着意刻画山石肌理,而在意表现云雾缭绕的山林气象。

雪舟等杨,《破墨山水图》(局部)。
重点来了,想象一下看惯了金碧辉煌的狩野屏风的商人赞助者们,如何能够忍受单色又抽象的水墨作品?当然,审美虽然一时难改,附庸风雅之心还是有的,这些有钱的赞助者也不甘心只在家里悬挂金碧辉煌的屏风,毕竟他们也需要一些文人元素妆点厅堂以体现文化修养。英国艺术史学者Timon Screech发现,极具商业头脑的画家池大雅(1721-1776)即运用了上述第一种方式,以传统形式绘制文人题材作品,以迎合商人品味。其《楼阁山水》绘制于金碧辉煌的屏风,乍看之下格外浮夸。然细细观察即可发现其绘制的内容为典型的文人画题材:致仕文人纵情山水,与友人谈笑风生,饮酒作乐,另有童子捧琴在旁,似乎随时准备高歌一曲。画中以用墨为主,尽量减少色彩的使用,却仍保留了一定的设色,这样既不会显得太俗气,也不会高雅到让附庸风雅的商人无法欣赏的地步。此作品虽然所绘主题仍为“胸中丘壑”,却早已背离了文人精神。池大雅生于京都,父亲是个下级官员并在其四岁时即过世,后来他开设扇子店,通过临摹中国传来的木刻版画画谱学习绘画,此部分在下文还会提到。在南画界,池大雅被归为第二代南画家,他师从第一代南画家祇園南海与柳里恭(1704-1758)。虽然池大雅常被视为是南画的集大成者,他终生以卖画为生,在本质上与职业画家并无太大区别。

池大雅,《楼閣山水図屏風》。
寻找稳定的赞助者对于南画家而言并非易事。江户时期崇尚汉学之风虽然起源于将军和幕府中的儒师,而儒学风气也在町人(即市民阶层)中间流行,町人中的商人、作坊主、旅馆老板、小店主和城市手艺人,才是南画的消费者。这一现象实际不难解释,江户时期其他画派实际已和社会各阶层紧密挂钩,例如土佐派和旧权贵、狩野派和武士与将军阶层相关联,只有中国主题风格的南画尚未被某一阶层霸占,故处于社会最底层却掌握雄厚财力的町人时常会慷慨出资购买,以提高自己和后辈文化教育水平。著名艺术史学者高居翰(James Cahill)最为推崇的南画家与謝蕪村(1716-1784)算是较为幸运之人,他的画作始终有其稳定的市场。与謝蕪村出生于大阪的富裕农家,早年接受诗歌而非绘画训练,后来成为名声显赫的俳句诗人。绘画是他维持生计补贴家用的方式,大部分买画者都是向他学习诗歌的学生,或是通过他学生、友人买画的富裕市民。蕪村为了维持自己和全家的生计,画了大量屏绘、祝贺图用以出售。例如京都的“岛原角屋”即是一间稳定赞助蕪村生活的茶馆(也是一种青楼),一直替他维持生计,蕪村很多绘画作品都是为其创作。其中《武陵桃源图》描绘了4世纪诗人陶渊明偶入桃花源的故事,島原角屋利用此作进行宣传,意在使顾客体悟到在这座茶馆中就彷佛置身桃花源一样,可以得到审美和情色两方面满足,渔人即将进入的子宫般的山洞亦含有性暗示。可见芜村十分擅长使自己的绘画风格服务于商业目的,他也清楚地知道消费他画作的人希望看到什么。

与谢芜村,《武陵桃源图》,1781,京都角屋藏。
第二种提高画作价钱的方式是以文人理想或创作时的“南方状态”当作卖点,换句话说,原本被作为文人画追求的理念也会成为商业的噱头。江户时代幕府统治下,跨阶级流动与交往非常困难,文人在工作状态中需要时刻保持警惕,以避免做出不符合其身分地位的举动。“醉画”、“合作创作”则作为工作之余的休闲活动,给予了一种不同身份(包括不同阶级、性别)人士往来的渠道,以及入世生活中短暂的自由,文人由此达到南方状态并实现文人理想。“醉酒”状态作为一种短暂的“南方状态”,给予文人逃离白天“北方”生活中严密行为规范、森严等级秩序以到达自由之境的渠道,“醉画”也因此成为一种典范。画家浦上玉堂(1745-1820)曾宣称自己在绘制一幅巨幅作品时先后经历了十次醉酒状态,他在很多画作题款处也都声明自己是醉酒状态下作画,不过他是否真的喝酒十分可疑,很有可能是希望通过延续自己创下的典范为作品赢得稳定买者。就连上文提到的与謝蕪村也难逃一劫,他于1760年绘制的《仿王蒙山水》六条屏的题跋上声称自己创作时已经微醺,而高居翰认为这只是为了掩饰他作品的不成功罢了,他虽然努力尝试使用“超逸”的笔法,却还缺乏通往成功所必备的扎实技巧。

与謝蕪村,《仿王蒙山水》,1760,京都国立博物馆。
南画家群体另可通过“合作创作”取得一种群体内部的平等,这种合作创作可通过一人作画、另一人题款,也可通过多人轮流作画,由每人绘制部分图像的形式完成。例如釧雪泉(1759-1811)、谷文晁(1763-1841)等人曾共同创作一幅怪石图,每位画家绘制其中一行,在纪念群体友谊的同时给予个人独立创作空间。不过此类原本为了宣扬自由平等的即兴创作常常会变成商品在文人聚会结束后直接交易。例如自18世纪末,皆川淇園(1735-1807)即开始组织一年两次的书画会,画家们的即兴创作也不局限于南画,不过参与者都是“文人”,被视为粗俗的浮世绘创作是绝对不会被接受的。皆川淇園声称聚会是为了发现画坛新秀并使其具备竞争力,这本身即违背了文人理想,当创作与买卖和竞争相联系时,这类画家聚会就失去了初衷。皆川淇園似乎也很清楚文人画家与金钱关系过于紧密不是件好事,他曾努力解释自己并没有私吞聚会卖画的利润,而是将这部分钱全部用于与友人畅饮。

彭城百川《树下斋》。

倪瓒,《容膝斋》。
既然南画承袭的是中国文人画,日本南画家又是如何取得图像进行学习的呢?实际上,无论是中国文人画家还是日本南画家,他们都知道宋元绘画才是中国绘画的巅峰,然而南画家基本没有机会见到宋元书画真迹,他们取得图像只能仰赖其他渠道。高居翰曾概括出三种模式:第一,通过中国传入日本的木刻版画印刷画谱;第二,通过流入日本的明末清初绘画,这其中又分为以商品形式流入的作品以及通过佛教寺院流入日本的作品两类;第三,通过与造访日本的中国画家的接触,这些前往日本的画家实际上在中国只是二流甚至不入流的画家。然而,一位优秀的艺术家若希望学习外国绘画风格的精髓,最行之有效的方法还是临摹精品绘画真迹,这是以上三种模式均无法提供南画家的。
具体而言,首先,中国木刻版画画谱传入日本对日本文人影响极大,这也是研究南画图像来源时历来被认为是重中之重的面向。此类画谱当然不会完整复制画家的整幅作品,而是通过解释画家作品中的典型元素和技法指导阅读者进行练习。此类画谱在明代即出现,如万历时期的《图绘宗彝》(1607),天启时期的《八种画谱》(1621-28),而最为知名的是清康熙年间王概三兄弟所著之《芥子园画传》(1679-1701),于18世纪初流传至日本。无论文字记载还是传世作品都可以证明众多南画家皆模仿过此类画谱,例如在南画的三位开派人物之一彭城百川(1697-1752)的画作《树下斋》中,发现其明显受到《八种画谱》的影响。Timon Screech发现,百川的《树下斋》与倪瓒(元四大家之一)的《容膝斋》惊人的相似,画面中均不见任何人物,茅屋运用双色进行描绘并且十分低矮,这些皆是倪瓒惯常使用的格套。彭城百川并未见过倪瓒真迹,其图像来源比较可能是通过参考《八种画谱》,其中一构图及其类似的扇面绘画可以解释其作品为何将倪瓒的直幅纵向构图改为了水平构图的横卷。当然,印刷品所无法传达的是文人画家对于笔墨的表现,这可以解释彭城画作中为何以湿笔取代倪瓒的渴笔。
不过学者们往往太过强化中国印刷画谱对于江户美术的影响,高居翰指出,上述的第二种图像来源,即传入日本的明末清初绘画也需要被格外关注。传入日本的明末清初绘画可被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以商品形式流入日本的画作,这类画作经由中国商人买卖,由长崎进入日本,长崎的贸易记录可以证明当时流入日本的此类画作为数颇多。这即意味着,日本收藏家在真正理解中国画作以前即已展开了收藏工作,他们所收藏的中国画作是对中国商人拣选的作品的再次筛选,因此在书画贸易中主动的选择权掌握在中国商人手中。而中国商人选择的书画并非具备较高艺术价值的作品,而是那些相对便宜、易取得,且一眼望去又有一定吸引力的作品。虽然大多数南画家并不愿承认自己模仿的是明末清初的次等作品,但由于别无他法,他们仍然不得不透过这类作品进行学习。例如与謝蕪村的《象头山图》即是仿照晚明苏州二流画家钱贡的风格而作。第二类作品为通过黄檗宗(日本佛教的一个宗派)流入日本的中国画作,福建画家绘制的宗教画作接二连三地在日本黄檗宗寺院被发现。宗教画之外,山水画作也透过黄檗宗僧人被带入日本。从僧侣的诗作中可以发现由此渠道进入日本的山水画包括唐寅、董其昌等人的作品。日本黄檗宗的始祖隐元隆琦(1592-1673)未公开的私人收藏清册中甚至包括了赵孟頫的马画,以及陆治、蓝瑛等人的作品。

与谢芜村,《象头山图》。
最后,南画家还可以通过与造访日本的中国画家进行接触学习绘画,不过这些画家在中国画坛却处在边缘地位。前往日本的黄檗宗僧人中本就有许多业余画家,不过他们的作品在南画发展中并没有扮演主流角色。除此之外,其他活跃于日本江户画坛的还有清代商人画家伊浮九(1698-1747),他自1720年起多次造访长崎。他并无自己的创作风格,只是保守地模仿中国文人画,但是由于日本南画家缺乏判断力,仍视其为“舶来四大家”之一,并将其当作学习的对象。另一位更具知名度的为造访日本的中国画家为沈南苹(1682-?),他于1731至1733年在长崎居住,并将院体花鸟画传入日本,他的追随者众多,构成了“长崎派”中重要的一支。
由此可见,Timon Screech虽以“心中之画”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南画的核心理念,然而南画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了这种理想,仍然值得细细体会。南画虽然是反院画而生,然而画家也必须要生存;由于南画的赞助者多为市民阶层,画家的创作也就自然地融入了市民品味。此外,即便是创作“心中之画”,也需要图像来源,而南画家所能见到的主要是中国画坛的次等图像,可供他们学习的资源十分有限。当然,南画在日后也发展出了不同于中国文人画的特色,不过这并非本文探讨的重点。

今村紫红,《热国之卷》(局部)。
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明确,江户时期虽然画坛氛围相对而言变得较为活跃,占主流地位的仍为传统院画,南画在江户时期却并未发展壮大。有趣的是,若将时间轴线拉长,即可发现南画在20世纪初对日本主流画坛的影响甚至要大于江户时期。1910年代与1920年代的日本画坛产生了两个新思潮:“南画的再评价”和“东洋回归”思潮。南画在明治(1868-1912)初期一度被认为是过时的艺术,呈现衰退现象;而到了大正時期(1912-1926),很多画家开始尝试重新从南画中汲取创新要素。1910年代后的日本画坛,常出现将文人画与印象派、后期印象派画家画风比较的说法,例如1911年藤岛武二(1867-1943)指出高更、塞尚和梵高的作品与南画家池大雅、与謝蕪村、曾我萧白的绘画,从心理学观点可以找到共通之处;1922年万铁五郎(1855-1927)提到塞尚、梵谷作品中的笔触、色彩以及构图的律动和南画的笔韵、墨韵有共通之处,并指出南画的理想在于表现由精神所支配的肉体律动。1920年代日本画坛也出现“东洋回归”的主张,许多东洋画画家重新从南画中寻求创新要素,例如今村紫红(1880-1916)结合后期印象派形成了新南画风格。江户时期处于边缘位置、代表市民品味的南画,如何在大正时期民族主义思潮下成为探索日本绘画主体性的灵感来源,这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
- 上一篇:欧洲画家提香的遗产 受惠后辈大师
- 下一篇:印象派们在伦敦 流亡中的法国艺术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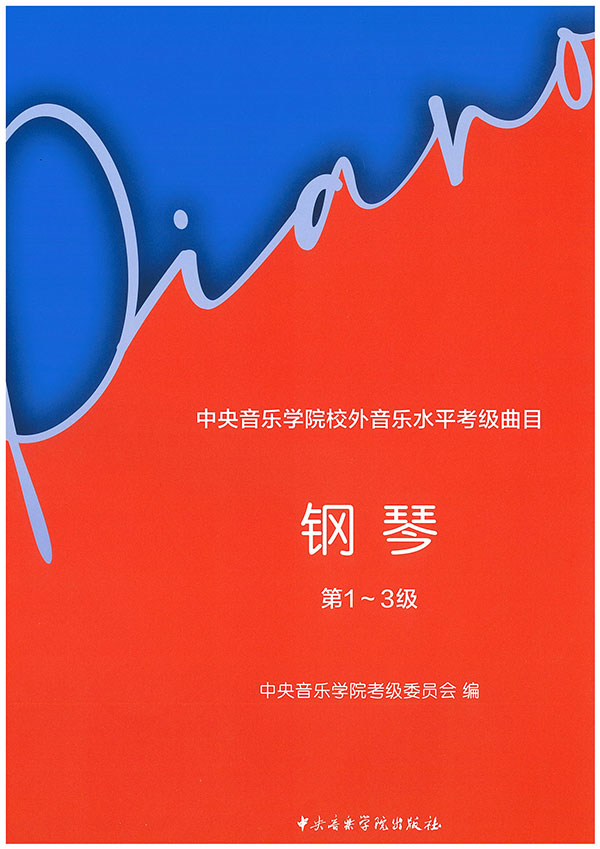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