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丹红谈音乐教育专业学科建设与愿景
余丹红,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市第十、十一、十二届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委员、九三学社上海市委青年委员会副主任、上海音乐学院支社副主委、国家教育部义务制教育教材评审专家、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学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九三学社上海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记者采访了上海市政协委员余丹红教授。

林尹茜:您毕业于音乐学系西方音乐史专业,是上音培养的第一位音乐学女博士,研究课题聚焦于美国先锋音乐家,在音乐学领域有很大发展空间,为何选择在音乐教育系工作?
余丹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读书所选择的专业与就业是否保持一致,这得看每个人的机遇。很长时间里,我对音乐学的感情挥之不去,毕竟浸泡在音乐学领域时间颇长,也能找得到研究的感觉,学得非常轻松而愉快。1999年江明惇院长提出建议,让我到音乐教育系工作,虽然有人说这个专业一穷二白,但我觉得只要认认真真地做,踏踏实实地教学,是可以建设的积累的,所以我发自内心地高兴并感激,欣然前往。我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我在讲台上有较好的掌控力,可以成为一名好教师。假如今天再让我选择一次,还是会选择教师这一职业。
林尹茜:音乐学的学习经历对您目前工作有哪些帮助?
余丹红:给了我很好的学科训练:首先是专业知识的积累,音乐学涉猎的面比较广泛;其次音乐学注重思维方式的训练。在此基础上,给学生讲课比较游刃有余。另外,体系化概念是音乐学学习留给我的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这种思维方式使得我对音乐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产生最初的思考,并在后面的实践中,体系化概念的作用一直是十分有效而明显的。
林尹茜:1997年教师教育专业以音乐教育系之名恢复建系,您当时在音乐教育系的主要工作?
余丹红:我当时同时开设了五门理论课,还附带教钢琴。外籍教师来了兼做随堂翻译。记得最辛苦的时候,给德国奥尔夫基金会委派的教师沃尔夫冈·哈特曼连续做了一个月的随堂翻译。到最后几天,哈特曼还是精神振奋地站着上课,而作为翻译的我基本上累得坐在地上。
林尹茜:哈特曼教授对您和音乐教育系的影响?
余丹红:给哈特曼教授做翻译,他的理念通过我转译给学生,这个过程就等于自己系统地学习了一遍。课余时间,我会跟哈特曼探讨他的上课内容,出于音乐学研究的习惯,我解构他的课堂内容:为何选择这样的素材?为何选择这样的方法?动机与目的是什么?当时的想法也是简单,自己必须先弄清楚,然后在课堂上翻译才能够说得清楚。这样,慢慢建立起奥尔夫教学法的基础。可以说,我本人关于当代音乐教育理念的最初概念,是哈特曼启蒙的。
当时学生的兴趣不在这,基本上都是抱着作表演艺术家的念头进入上海音乐学院。我觉得这是当时音乐教育专业最大的弊病:学生普遍失去了哲学意义上的“我是谁”这个核心概念,他们没有学科意识,普遍地“反认他乡是故乡”。在哈特曼上课过程中,一些学生有抵触情绪——这个有什么意思?素材都很简单,卡农、固定低音、即兴,在他们看来都是随手拈来,没有所谓的艰深“技术性”。有时候,老师要求配合,很多人显得慵懒。我就十八般武艺都上,自己弹钢琴即兴,凑乐队人数。这样,台上无比忙碌的我,渐渐赢得了学生们的信任。比较有意思的是,当初这些有抵触情绪的学生们在毕业之后陆续回来要求旁听教学法课程,尤其是哈特曼教授来访时,更是门庭若市。因为在实际工作中,他们终于发现这门课程对于教育专业的重要性。
江明惇先生在恢复建系之初的国际化道路选择,对音乐教育专业未来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奠基意义。起步阶段,德国奥尔夫基金会对我们帮助意义重大,他们让我们从教学法入手,看到了完全不同于传统音乐教育新方法与思维。这使得音乐教育学科建设站在一个崭新的起点上。
林尹茜:20世纪90年代末,去美国学习又回国的音乐人不是很多,为何您一次次到了美国,又一次次回来?
余丹红:1997、1998年,我为了博士论文写作,到美国生活了10个月。刚去的时候不太敢开口说话,美国英语与我们的英语教育背景差距较大。所幸我的资助人是语言学家,她会说11种不同的语言,包括中文。她对我的语言训练提出了一些比较严格的要求,老师的语言十分清澈而标准,就像希拉里·克林顿的那种发音,那种受过很好教育人的发音。
1990年代末,美国给我比较强烈的震撼。那种物质上、学科知识上的繁荣与周全,令我产生一种几近绝望的感觉:他们把能够做的都做了,在他们的社会里,我们能够做什么?也就是这个疑问,使得我逃离。我的资助人最不理解的是:你为何一去不回头?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我是一棵记忆深刻的植物,我属于我自己的土地。别人的好处我很欣赏,但是我不介入。
我很高兴,我所有的生活状态都是我自己选择的。这是我人生中最有意思的一点。比如,我的家庭不是音乐背景,但我选择了音乐作为职业。当时人家都说美国好,我选择了回国。大家都觉得我不应该到音乐教育系,但我又选择了。总之,我选择了我自己的人生,我为此感到深具价值。
林尹茜:从教师转为教师兼管理者,作为管理者的思维方式有何不同?
余丹红:音乐教育系当时的师资力量欠缺是显见的,但面临的最重要问题自然是学科建设。我在2001年曾经投稿一篇文章,参加中国教育学会的音乐教育论文比赛。文章核心内涵就是关于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科建设问题,我大胆提出音乐教育核心专业主干课程,应该由音乐教育学理论与实践系列课程构建:音乐教育学导论、音乐教育心理学、音乐教育史、音乐教学法、音乐教材教法与教案写作、教学见习与实习等,而不是传统钢琴专业、声乐专业。所有的乐技能对音乐教育学生而言,是工具不是目的。这个观念在当时引起了较大反响。杨瑞敏理事长多年后还跟我提起这篇文章曾给她留下深刻印象。
我当时比较坚定地把教学大纲给修订了,因为这关乎专业的定位与目标问题。当时这么做的风险是显然的:这些构思中的专业主干课程几乎没有现成模板,一切都要从无到有建立起来。我们搭建了一个理想主义理论框架,接下来,教师培养、教材写作,成为当务之急。所幸,十几年下来,这一切都已经进行得十分顺利,有了可靠的教师队伍和实用教材,从招生到教学到毕业和继续升学,建立了一条良性通道。
林尹茜:目前音乐教育专业最大的困境是什么?有何解决途径与方法?
余丹红:中国音乐教育专业的困境来自内外两个方面。一是音乐门类中其他学科对这个学科带有偏见性看法:读书成绩不够优秀、专业能力不足的学生才会考音乐教育专业;该领域没有体系化的学科构建和研究实力;该领域谁都可以发表意见,个人化的经验可以代替学科理论;该学科不像钢琴、声乐表演,可以参加世界比赛拿奖,这里出不了世界一流的标杆式人才,不值得花太多精力与投入。二是来自音乐教育学科内部:基础薄弱,学科积累较少,体系化工程急需建设;人才素质参差不齐,研究能力亟待增强;理论能力与音乐能力不匹配;学科观念出入太大,很多基本常识仍然会有不认同声音,信息不够通畅;学术氛围不够,讨论学术问题很容易陷入个人经验主义泥沼;对国外研究状况了解不深,以偏概全……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国家决策领域里,是否意识到音乐教育的社会价值?是否意识到音乐教育对一个完整人成长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对精神世界的构建、对人格的完善,以及思维方式的建立等有其独特作用?是否觉得应该扶持这个专业?当年匈牙利的柯达伊是得到国家层面大力支持,他的全民教育观念、音乐教育体系才得以顺利推广。在我国,申请课题时,音乐教育和别的学科之间,倾向性还是有的。学科歧视,客观存在。
林尹茜:音乐教育系师资队伍建设与管理如何?
余丹红:音乐教育系是年轻人占主流的系,都有良好的专业背景,对自己专业有追求,更多地将目光聚焦于专业能力提升之上,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气氛。在教学、表演双重兼顾前提下,每个人都有很不错的科研成果。如钢琴和声乐教师十分注重对声乐和钢琴教学研究,以及如何培养学生教学能力,很明显区分于钢琴系和声乐系教师的关注方向与学科侧重。
从管理角度而言,对教师采取短期放飞政策,让他们轮流出国访学,一般不超过一学期,让他们在最短时间内获得尽可能多的能力。回国一段时间后再找机会继续深造。来回几次能力提升十分明显,而且比较安全不容易人才流失。
林尹茜:上音音乐教育专业有哪些专业成果的展现?
余丹红:首先,我们参加了国际最大行业学会——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并积极承接大型国际会议,如2009年亚太地区音乐教育研讨会和2010年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专业音乐家教育分会。跟国际行业学会合作,意味着我们的国际化眼光和接轨能力,同时,在引进国外理念的同时,也展示我们自己。其次,我们对学生专业基础能力十分看重,参加教育部“珠江杯”五项全能基本功大赛,囊括个人冠军和团体冠军,女声合唱团参加3届世界合唱比赛,获得6枚金牌,以及女声合唱组别的金牌冠军。
林尹茜:您个人理想中的音乐教育领域应该是怎样状态?
余丹红:这个问题相当具有乌托邦意味,做一个理想主义的展望倒也未尝不可。首先,在国家政策层面上给予这个学科必要的重视与关怀。其次,建立一个经得起推敲的学科理论框架,学科领域著作丰盈、硕果累累。第三,出现一批有真知灼见的理论家和研究者。第四,从事音乐教育的人才音乐基础扎实、眼界开阔、理论修养全面、能够担当教育者这个称谓。第五,该学科领域从业者深具涵养,彼此团结友好共同推进学科良性发展。
林尹茜:请问您的社会活动对您的专业发展有帮助么?
余丹红:我社会活动比较少,最重要原因是时间有限,我花很多时间从事教学和科研活动。当然,上海市政协委员身份对我专业发展有很大帮助。政协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沟通与交流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可以畅所欲言地提出我的专业诉求,而且也得到一些积极回应。例如,我们合唱团最初的国际比赛参赛,就是通过政协帮助,得到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的支持而成行。对此,我始终充满感恩之心。
- 上一篇:那英三首被周杰伦唱红的歌曲 其中一首竟因太火被禁
- 下一篇:就像木匠一样做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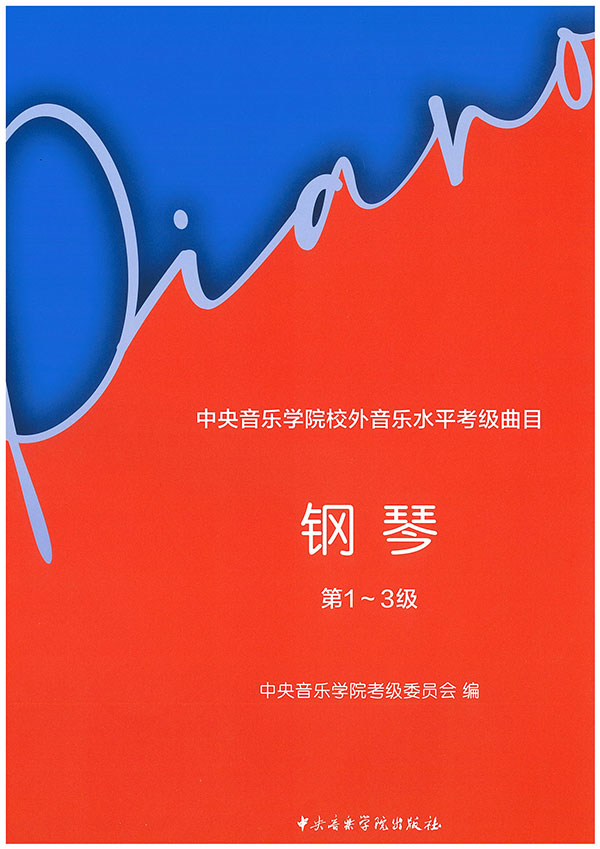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