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主义到公共政治:中国现代艺术的价值出口
另 则,简单地将自由主义归结为“二元对立”也不免陷入了教条主义的误区。穆勒原则13告诉我们自由主义实质上是一个“群己权界”的关系,亦即在个体与社群之 间寻找一种责权对应的价值平衡。而哈贝马斯认为,除杜威以外,穆勒是康德之后分析了公共领域的原则和开明舆论对监督议会应起的作用的思想家之一。普特南则 明确指出“穆勒和杜威差不多,都重视积极参与民主进程的各个方面”。14除此,还如托克维尔,亦是主张自由主义的同时还强调政治参与。如此来看,自由主义 并非一定是“二元对立”的,从哈贝马斯、穆勒、杜威及托克维尔的实践来看,恰恰是反二元对立的。但你能说,他们都不是自由主义者吗?何况,现代性的危机之 一——重权轻责更是为哈贝马斯的公共实践理论创造了契机。特别是对于当下中国而言,一方面单纯地回到天赋人权或自然权利向度上的现代性无异于天方夜谭,另 方面现实又几乎普遍认同并全然接受了后现代及其虚无主义。在这一处境中,哈贝马斯的批判与实践理论无疑更具有建设性意义。
再则,王新将哈贝马斯归为后现代主义并不合宜。事实上,哈贝马斯真正反对的恰恰是后现代立 场。如施特劳斯所说的,后现代非但没有对现代性的种种危机形成制约,反而推进了这些现代性危机,以至于沃格林将其归结为是在一种“没有约束的现代性”。因 此,哈贝马斯固然批判自由主义,反对现代性,但是,他所反对和所批判的并不是现代性和自由主义本身,而是二者在演化过程中引发的各种后现代质变。所以,他 批判抽象的同质化的权利,主张从实践的层面上重新回到启蒙,重构权利的社会合法性和价值正当性。正如他所说的:“权利只有通过被行使才能被‘享受’。”15
感谢王新同学提出这一个关键问题,使得笔者借此机会能作一回应与澄清。说到这里,我们虽然不 能否认自由主义与公共政治之间存在分歧与张力的可能性,但是,设若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公共政治的实践非但没有对自由主义形成制约,反而积极地推进了现代 性理性与建设性。就像美国新左翼、新右翼,固然对现代性形成批判和指责,但这种批判和指责并不是制约现代性,而是积极地将现代性引向并竭力推进其正当的进 路。
与公共政治相关的论述主要还有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16其源头皆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政 治学》。在他关于城邦政治的论述中,提出真正的自由民即公民是指具有参与司法事务和政治实践的人。公民享有自由是基于城邦这一实存前提下的,亦即:国家先 于个体而存在。贡斯当将其称为古代人的自由。与之对应的现代人的自由则是基于自然权利、天赋人权前提下的自由,国家则是基于个体间的社会契约和政治信托建 构而成的,即:个人先于国家而存在。而社群主义或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也是因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失衡所致,由于过于强调个人权利,所以无形中弱化甚至 失却了对国家的公共责任和道德关怀,而公共政治实践正是意在平衡这一关系。需要赘述的是,在此不管是公共政治实践,还是社群主义或共和主义,都须有一个自 由主义的价值底色。17
其实,这样一个价值前提决定了公共政治对于当代中国并非没有意义。因为缺乏自然法、自然权利 传统,所以单纯地强调自由主义很容易陷入个人主义的异端,而公共政治的有效实践为自由主义的平衡性建构提供了必要的支撑。因此,我们意在建构的并非是一个 单纯的权利向度,而是一个在道德、法律制衡下的权利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并非绝对地斥责本土化、后殖民,反对社会学转向和正当性质疑,而是主张在自由主义的前提下,基于现实考量,反思性地、适度地予以审视、关照和参与。按哈贝马斯的逻辑,正是这一公共性实践,为我们回到启蒙、回到现代性建构立场创造了可能。
3.从立场到实践:价值的平衡
贡斯当看来,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本质上并不是背反的。相反,其实是一种互补的对应、平衡关系。也就是说,自由主义与公共政治(或社群主义)貌似对立,本质上则互相依赖,互相支撑。作为一种立场,自由主义决定了公共政治实践的正当性。反 之,公共政治实践也为建构自由主义的政治正当性创造了可能。因此,公共政治向度上的现代艺术实践无可非议,关键在于这样一种实践是否是建基于现代性或自由 主义建构的价值背景。而这一判断,针对的恰恰是中国的现实情境。
显然,这一前提下,笔者真正反对的是当下失却自由主义前提或自由主义底色的那些极端的左翼、右翼,而近年来此起彼伏于当代艺术界的本土化反思、后殖民批判、社会学转向及正当性质疑等思潮皆未能摆脱这两个异端。不可否认,这两股势力的起兴对于中国 现代性的破坏性远远大于其建设性,消极性远远甚于积极性。事实上,中庸(moderation)就是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则。“它使我们接受下述事实:大部分 不同群体的理性人绝不真正处在一个相同道德框架之内。在面对其他人的合理申述时,最理性的就是相互调整为各自的申述,消除分歧,并至少向某些分歧妥协”。18因此,从个体到公共,二者之间的交替、平衡、妥协、互补才是中国现代艺术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出口和新的进路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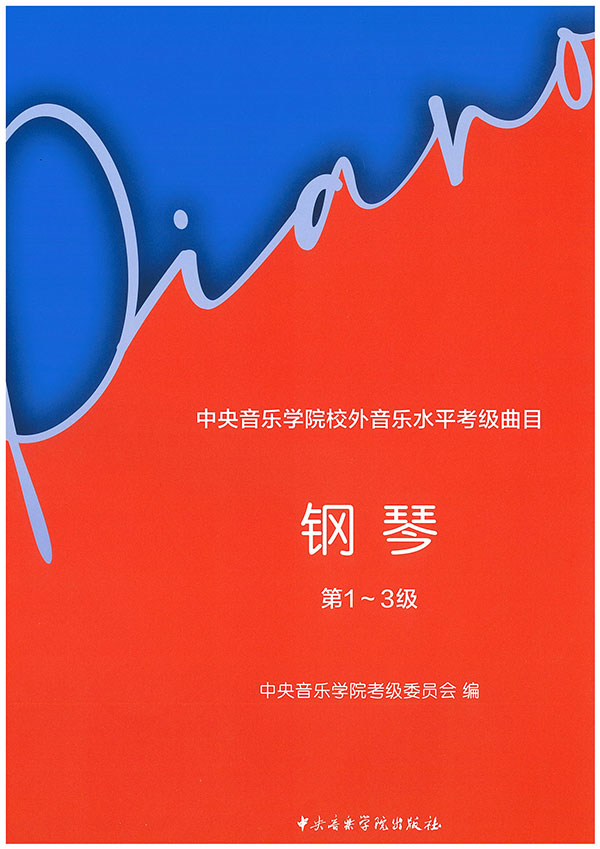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