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主义到公共政治:中国现代艺术的价值出口
正是在这样一个立场背景下,笔者力图将中国现代艺术的大众化思潮这一本然的思想史问题置于中国现代性反思的价值框架和思想视域中。事实是,通过这样一个考察,我们也的确探得并揭示了其背后问题的复杂性种种。
二 方法问题与研究现状
当然,这样一种思路难免引起误解。最普遍的一个质疑就是,这一西方思想史的路径、立场和方法 对解释中国问题是否有效?或者说是否可能?去年,课题的部分成果在由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今天的85:85新潮美术运动学术研讨会”和由中央美术学 院《美术研究》杂志社主办的“2007当代艺术批评与理论研讨会”上先后发表后,便引起与会者的怀疑。在我们看来,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支撑正是西方思想史背 景、立场和方法。对此,我们更认同甘阳的说法:“只有深刻地理解了西方,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国。”19笔者对西方的阅读、思考正是为了更具深度地审视、关 照和认识中国问题,西方思想在此只是一个认识的契机、途径、方法而已。穆勒还说过一句话:“自由主义的最高原则就是功利主义。”既然西方思想更有利于我们 认识自己,“拿来”有何不可呢?说到底,方法本身并不重要,方法的最高境界是没有方法,一旦方法成了目的,则无异于舍本逐末。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 不能揭示问题,澄清真相。何况,二十世纪的中国又何以能够摆脱西方,而单凭自己传统和历史经验来认识理解自我呢?更不用奢谈什么建设性创见了?!
迄今,国内关于中国现代艺术研究的论著也已出版不少,但普遍以通论性的资料梳理为主,包括郑 工的著作《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广西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黄宗贤的《大忧患时代的抉择——抗战时期大后方美术研究》(重庆出版 社,2000年版)、黄宗贤的《抗日战争美术图史》(湖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吕澎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7年版)、邹跃进的《新中国美术史(1949-1999)》(湖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等。关于艺术大众化思潮的研究,相对贫乏,屈立丰 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现代美术的大众化思潮》(2004年)、韩劲松的硕士学位论文《二十世纪上半叶美术大众化思潮嬗变》(2004年)及高天民的博士学 位论文《中国大众主义美术》(2004年)对此作了系统研究。相关的研究论文主要有宗贤的《大众化美术思潮与中国画变革》(《贵州大学学报》,2002年 第2期)、谢洪波的《略论20世纪美术大众化历程》(《艺术探索》,2004年第4期)、刘赦的《图象与新知——〈点石斋画报〉与美术大众化》(《南京艺 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5年第4期》)等。这些著述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点和文献资源。
通过阅读这些既有的研究成果,发现其普遍停留在文献清整的层面上,以至于研究无形中与整个时 代的政治文化背景相脱离,而缺乏一个价值层面或思想进路中的深度探讨和考量。当然,纯粹意义上的实证研究并非没有意义,相对而言其更符合历史研究传统。但 是,对于艺术史而言,若缺乏事件性背景的支撑,单纯地依靠作品堆砌和简单描述很难赋予其生机。反之,正是通过各种可能的解释,其才会变得更具活力和生命 感。否则,再怎么还原,也只是一具僵尸而已。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所说的:“一种不带价值取向的历史编篡要么只是资料汇集和史学本身的预 备,要么——倘若它自诩为名副其实的史学——给人枯燥无味的印象。”
黄仁宇在《如何确定新时代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一文中认为,一个学人如对博丹、马基 雅维里、霍布斯、洛克、亚当.斯密、马克思、卢梭和黑格尔等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家思想有了充分了解和掌握,那么,他对中国近代史之展开,必多积极性的看法。21这一点,笔者显然与先生不谋而合。某种意义上,他的这一洞见也成为我思考视角和认识路径的一个支撑。最近,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了蒋介石日 记。看过日记的诸多海内外近代史学者得出一致结论:《中国近代史》应该重写。杨奎松在他的近作《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便提出,以往的党史研 究大多是站在中共的立场,所应用的文献资料也仅限于这一方。22为此,他通过查阅、收集大量国民党文献,站在国民党立场,就此探得诸多新的真相细节,修正 了不少既有的历史“定见”。这便告诉我们,中国现代美术史的研究同样不能只是停留在中共一方的资料文献,或许正是在国民党的文献中,我们会发现历史不为人 知的另一面。事实上,我们在研究中,特别是面对所收集的大量早期革命时代的文献时,因为其本身的局限,看到的几乎是一边倒的声音,以至于我们在选择材料时 常常犯难。这就需要通过另一方即国民党、乃至日方文献的对应比证,由此才可能将历史引向深入和复杂,而非翻来覆去只有“图存救亡”。所以,文献的局限使得 很多问题的论证不免牵强。相信,随着国民党、包括日方等更多文献的逐渐公开,我们的研究也会不断展开和深入。
从立场到方法,笔者深知这样一种思考和论述无不潜藏着危险。不过,这些危险事实上也是能够料 到的。但之所以未能避免,也是因为无法避免或不可避免。不可避免也总归有它的道理。因此,与其说这是一部学问之作,毋宁说,它实是一部问学之作。诸多观点 可能不乏论战性,谨此也希望诸位专家、同仁不吝批评、指正!将这一问题引向更为深入的讨论,才是我们真正所期待的。
全书分为“启蒙与革命”与“启蒙与消费”上下两篇,分别以1919-1977、1978-2000年为界限,按照身体、空间、集群心理(艺术运动)及话语(命名)四个角度展开论述。这并不是说,上下两篇没有关联性或连续性。之所以分 开论述,也是因为两个时期前后的侧重不同。上篇讨论的二十世纪初、中期侧重于革命,下篇针对的后期更倾向于消费,但二者共同分享了一个价值前提——启蒙。虽然,两个时期的启蒙几乎全然不同,但都不可避免地关涉到中西古今向度上的现代性问题。相对而言,前者更强调图存救亡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认同,而后者则更侧 重于公共实践层面上的个体权利诉求。这一划分并不意味着革命时代就没有消费。美国学者葛凯的新著《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所描述的正是近代 中国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和消费主义的兴起,致使民族主义者集体抵制外货的前前后后。23这就告诉我们,消费与反消费背后皆根植着民族国家认同这一价值基 点。但因消费本身就涵有现代性因素,所以,看似抵制外货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认同成为现代性表征,但实际上其还有反现代性的一面。不过,基于现代性悖论前提下 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最终却使革命政治吞噬了消费政治而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同样,这亦非意味着,消费时代就没有了革命。恰恰相反,中国的消费主义(不管 是革命时期,还是改革时期)不同于西方的正是其独特的革命底色,或者说其依然处于后革命时代。而此时的消费背后蕴含更多的是精神亏空和价值虚无。因此,它 并非是一个现代性之正当意义上的消费主义,其既具有现代性质素,亦不乏反现代性因子。这也证明了,百年中国尽管发生了几次社会转型,但背后根深蒂固的依然 是革命(后革命)的逻辑。
问题是,身体、空间、集群心理(艺术运动)及话语(命名)四个角度之间又是如何关联的呢?陈 彩霞老师一提出这个问题,便引起了我们的警觉。不过,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虽然这四者之间没有先后关系,但是自由主义立场与公共政治实践则一以贯 之于四个角度的论述。如果非要理出一条清晰的脉路,难免为了服从主旨,相互依存,反而会做一些“不合情理”的“加法”和“减法”。看上去,结构严密得“水 泄不通”,但恰恰因此,反而失却了一些难得的新见,甚至还画蛇添足,附加了一些不必要又无根基的“支撑”。这似乎也成了现代学术的一条通则。不过,就像罗 素说的:“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绝不会完全正确,但是自圆其说的哲学满可以全盘错误。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向来包含着显眼的自相矛盾,但是正为了这个缘故才 部分正确。”24在我们看来,能否理出一条线索,得出一个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四个角度的繁复论述中,是否能够揭示出更多被忽略了的矛盾、冲突、悖谬 等仅属“部分正确”的历史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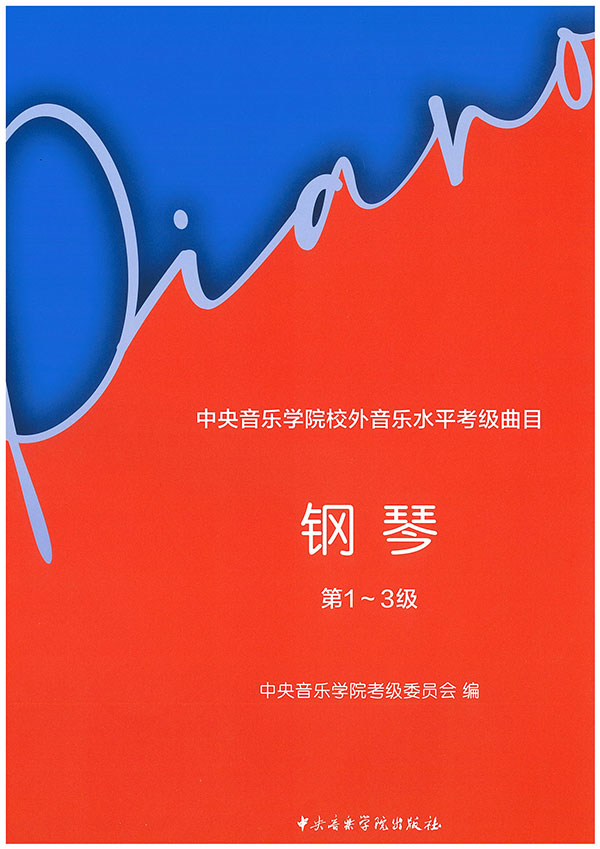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