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话(近代)
近现代书法——承明清之余绪
1911年的辛亥革命运动,推翻了中国社会长达2000余年的封建统治。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中国社会民主、科学的艰难历 程。但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段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军阀混战之苦。而从辛亥革命成立中华民国以后,中国人民为了争取民主 与自由,彻底消灭剥削制度,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又先后经过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
在这一时期,书法艺术也经历了它悲喜交集的历史,一方面它作为一种艺术门类,有独立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随着考古大发现,大量古代文字资料出 土,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养料;再一方面,印刷技术日益精进,为碑帖的流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这些都是值得“喜”的地方。而在反面,频繁的战争,又 造成了人民生活的困苦和大量珍贵文物的毁坏,书法艺术基本上成了一些富有人的爱好,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
承清末赵之谦、徐三庚等人的余风,民初书法篆刻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十分矛盾的发展心态。赵之谦是帮助我们理解民初书风的一个关键,在某种程度上 说,他的存在有类于绘画上从扬州八怪到任伯年的存在。赵之谦为民初人带来的不是一种风格的规定,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启示。在赵之谦之后的第一代人中间,我 们发现了两个杰出的典型,一位是沈寐叟,一位是吴昌硕。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典型:作为遗老,沈寐叟深深重视清代碑学所具有的价值,他不可能跨越这个历史的规定。但作为艺术家,他又具备本能的开拓希 望,因此他努力寻求在规定下的发展空隙,从一个清代人感到迷惘的风格夹缝中走了出来。在一时间,沈寐叟的北碑行草风成为民初书坛的一面大旗。
吴昌硕(缶庐)书法以篆书见长,尤精石鼓文,用笔结体皆朴茂雄健,古拙可爱,气度之恢宏厚劲,为几百年来仅见。如果我们把沈寐叟看成是以局部兼 全体,即以北碑法人行草这一风格类型为书法界提供一个具有全局意义上的典范的话,那么吴昌硕的方法正好反之。他是致力于全体再深入到各个局部:在绘画上他 是一代大家,在篆刻上是领袖群伦,他的艺术涉猎面铺得很开,以文人式的综合资养来出以书法,使得在书法一道中特别得心应手。吞吐自如,气象万千。而其隶书 古拙方正,并不取扁而佻的一路,也是一种十分厚重的形象。因此,沈寐叟以方胜,吴缶庐以圆胜;沈寐叟意在生辣,吴缶庐旨在醇厚。沈寐叟以小见大、以局部见 整体;吴缶庐则从大见小、从整体到局部。两位大家可以标志着民初书坛上的两种不同路数,当然是同样有高度的路数。
在沈、吴之外,康有为也是一位大家。不过论总体成就,康有为似稍嫌弱。康氏的摩崖书有开张之趣,比吴昌硕和沈曾植的内劲皆有不同,他也能较好地 把握自身风格的高度,但他的风格较为单一,有些作品出手较随便,风格语汇也较单调,纯度显然不足。相比之下,倒是康有为在理论上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他的 《广艺舟双楫》在尊魏、卑唐方面有着非常鲜明近于偏激的态度,这样的观点的确使后辈学子为之震动,并在寻求自身的风格取向时普遍以他的观点为准绳。当代诸 多大家在风格上的种种状态,很少有不受康有为的影响而成的。
我们可以把沈寐叟(包括康有为)看作是立足于清代北碑风系统内部的崛起者。他们的思想还是上承北碑传统--上承以阮元、包世臣等人为标志的清代 书法大统,而把吴昌硕看作是向北碑风系统外部寻求启迪的追求者--吴昌硕的尚篆隶,说到底也与清代学术传统如金石考据学、小学等相一致的追求,这使他不可 能逸出清代传统之外。但是,他那种追求诗、书、画、印一体化的追摹上古,却使他获得了更高的立足点。就诗、书、画、印一体化的尝试本身而言,也已有了赵之 谦这位先行者,相对于北碑风与篆隶风而言,这种文人性格浓郁的一体化方式更具有艺术性而不是小学、金石诸学的学术性。但既已有了赵之谦,吴昌硕的努力就未 必是独辟蹊径,关键是在于:吴昌硕从上古名作中衍生出一个以石鼓为基点的书画篆刻同步风格,这是他的胜于清代那些学问家也胜过康有为之处,而他在这种同步 中时时注意追求格调高古,不取丝毫油滑之态,这又使他必然胜于赵之谦。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同时在两个方面找到潜在针对对象:反对清代的金石家书法的不讲 形式却津津于求来历,反对赵之谦式的注重形式但稍过表面的飘动轻滑习气。应该说,他是取得了他所能得到的最大成功。这使他成为民初书坛上当之无愧的代表人 物。
以吴昌硕为标志,在民初书坛上形成了一个层次丰富、主旨各异的书法结构,并衍生出一些目标完全不同的书法集群。首先,是以上承清代北碑风正统自诩的书家群。李瑞清,曾熙为此中的代表。
李瑞清、曾熙在艺术追求上较近于康有为,他们邢以魏碑和六朝墓志为书法正宗,又加之他们皆在一地以鬻书为职,因此我们可以指他们为一种类型。沈 曾植本来在风格意识上也相去不远,但沈氏开拓性强、视点也高,故尔位置也截然超越于他们之上。李瑞清、曾熙可说是守成者,而且准确地说,是仅以清代碑学传 统为尚的守成者。另一些书家,从笼统意义上说也可归人此类,如同为光绪进士的赵尧生,虽活动区域不在上海,而是生于四川、官于江西,但在趣味-卜也近于北 碑,专攻《董美人墓志》。又如:善写隶书的伊立勋,虽然以隶闻名,与北碑的直接关系不大,但也取工整不苟、步趋古人的态度,十分注重正统形象,自然在思想 观念方法上也与之无异。
统观李瑞清、曾熙至伊立勋等人的书法,我们很容易从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去窥测当时的观念形态:从风格层次卜混,李瑞清如此注重剥蚀之态,不惜以 毛笔去摹仿刀刻痕迹,说穿了也无非是试图以极涩去救佻滑,这在当时显然足以赵之谦特别是徐三庚作为对比的。因此,对于李瑞清的糙涩,仅仅从趣味或技巧上去 指责他是十分轻松的;而要拈出他的特定针对对象,却要化一点气力。曾熙的平实虽不如李瑞清那么引人注日,但平实本身也即是反佻滑。由是,我们在除了吴吕 硕、沈寐叟这样的大师以外,看到了对佻滑的几种救弊:一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是置若罔闻。前者矫枉过正,但也同样使人生厌:后者却显得太过平庸而貌不惊 人。而再从观念层次上说,则不管是极端如李瑞清,平庸如曾熙,其实也还都是立足于书法作为学术、作为应用工具的认识起点。他们都缺乏艺术家自身的激情,也 没有多少表现绍基那样的文人式超脱,实用性对他们而言是保持生计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他们又不啻可以说是在较浓郁的金石考据、文字训诂、崇尚北碑诸学的 气氛笼罩下对实用的一种复归。
与北碑派书法在风格上相对应的,是另一批认识同处一个层次上,但风格截然相反的书家集群。我们可以指他们为回归唐法派。以谭延闿兄弟为代表。
谭氏兄弟的楷书不只是在形貌上追随颜真卿,虽然他们不脱颜氏窠臼,但与前辈如钱沣相比,更有苍劲雄浑之致;与同时稍前的翁同和相比,则在笔致老 辣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在尊奉颜体楷书的一系中,他们洵称是代表作家。在其后继之的如赵石(古泥)、商衍鎏、高时丰、冯开(君木)等,皆是一代风流。即使后来领一代风骚、在北京声名显赫的如齐白石、溥心畲,也曾浸淫颜体日久,并以此起家的。但在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个事实:倘若将民初书法家作一调查,少 时曾习颜、欧、柳者十之八九,而以北碑为启蒙者却绝少。但大多数都是在借用唐楷作为拐杖入门之后,即刻意转向北碑,其正安心在唐楷阵营内孜孜不倦地用功以 求大成的屈指可数。这一方面使谭氏兄弟的成功显得格外突出;另一方面也使得唐楷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基础的代名词而不是一种风格类型,似乎只有魏碑才有资格作 为高度而存在。
民初的书法除了这两大风格流派之外,还有第三个集群。由于这一集群的风格特征相对不强,而他们的身份却很特殊,故尔我们不从风格角度上去强求名目。
伴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一大批以忠君食禄为宗旨的旧式文人转瞬间觉得无所依傍。他们赖以衣食的皇帝--从光绪到宣统都丧失了任何权威,他们所面 对的也已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封建社会的环境而是资本主义色彩渐趋浓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迫于生存,他们难以再抱残守缺。但就主观上而沦,他们却无不 缅怀传统、渴望复古,这就决定了他们在艺术上也具有两面性:在炫耀古趣的同时又不得不对现实作局部的妥协,鉴于他们在书法上并不是一个宗旨相同的流派而却 实实在在代表了一个阶层,我们指它为遗老群书家。
遗老群书家大都是前清的各部衙的官员或是获取过功名的人。他们身在民国,但却以前清的遗老自居。沈寐叟曾为逊清布政使,民国后又立志不出,他即是地道的遗老形象。只是他的成就太高,我们在前面单独论到而已。有代表性的遗老书家大致有以下一些:
陈宝琛,曾为宣统皇帝太傅。书宗黄庭坚。张蹇,光绪甲午状元,翰林院编修,书宗颜真卿、欧阳询。宋伯鲁,光绪丙戌翰林,书宗魏晋。魏馘,光绪乙 酉举人,擅魏碑。章锓,光绪甲辰翰林,书学孙过庭。朱益藩(1861-1935),官至陕西学政,考试留学生阅卷大臣。沈卫,官甘肃主考,陕西学政,书尚 颜真卿。罗振玉,为甲骨文、金文研究的一代大家,书法兼善古体。孙儆,举人,以卜辞风格驰誉书坛。刘春霖为光绪甲辰状元,书尚馆阁之风。工同愈,光绪进 士,书尚欧阳询。朱孝臧光绪进士,书师颜真卿。郑孝胥,光绪举人,官至湖南布政使,书尚苏东坡。钱振煌(1875-1944),光绪进上,书重晚明诸家,钱崇威,光绪甲辰翰林,书宗唐法。等等不一而足。
纵观这批遗老书家,书法大都各有家风。以书风的广收并蓄而论,如孙儆的以甲骨入书;如罗振玉的擅金文;如魏馘的擅《张猛龙碑》;都是极有成就 的。至于不走北碑一路的,如张蹇的学唐、郑孝胥的学宋,也皆有极开阔的艺术视野。即此而论,我们的确很难在艺术上为他们规定一个圈子。倘若没有身份的相 近,他们很少有可能走到一个集群中来。
但他们在当时,却又都以某种相近的方式合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阶层。清王朝被推翻后,他们又都对新政抱抵触态度,以“不出”为保持自己节操的标志。但随着俸禄官职的一朝烟灭,他们也像旧北京的八旗子弟一样,一时间有衣食不饱之虞。为了生存,又对社会作姓出了某种妥协:不得不把斯文暂搁一旁,鬻书卖 文,以求温饱。对于这些进士、举人老爷而言,这样的转变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认识转变。遗老群书家们在政治上往往会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如朱孝臧当时曾与王国维 一起,为复辟大肆鼓吹;又如罗振玉、郑孝胥在三十年代还辅佐溥仪担任伪满洲国官职。前者还是中国政局中的新旧之争,后者却近于卖国,虽不能与汪精卫的卖国 相提并沦,也多为时寸人所不齿。因此,他们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存在往往更重于作为一个艺术阶层的存在。但后者即必须受前者制约,因此遗老群书家虽风格各 异,但作为艺术阶层,保守、陈旧的思想也使得他们难以出现领一代风骚的大家。沈寐叟在辛亥革命后即矢志不出,专心以学问艺术为尚,倘他也是热心为复辟奔 走,甚至为恢复清廷不惜投靠外强,我想他未必会有如此的成就。此外,如沈寐叟、吴昌硕都不是只会抱着祖宗遗业者。沈氏在赴日本考察学政前后,即有意新学,倡办工厂,造枪炮,派留学生出洋等,以求自强,像这样的政治态度都不是仅仅一介遗老所能为之的。
作为遗老群书家的对立面,我们又看到了一种文人群或学者群书家群体的出现。章太炎可称是学者书家的代表。
章太炎 (1869--1936),早年即参加同盟会,反对袁世凯,又讲学日本,主编各报,影响极大。但晚年倡国学,博通经史,专攻语言文学,书法 以朴茂古雅的篆书见长,作篆无错字误字,笔势蕴藉有典则,是地道的学者书法的代表。与他相近的如萧蜕庵,曾为同盟会会员,南社社友,也是以学问治篆学,颇 得古沉静穆之致。陈三立、黄节、柳诒徵、丁辅之等皆可归于此类。另一类文士型的书家,则可以李叔同、姚茫父、袁克文为代表。李叔同,早岁留学日本,善西洋 画,习钢琴,又引进戏剧,曾主演《茶花女》,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位杰出人物,其书法虽非专门,但早习晋唐各家、兼学魏碑,出家后专攻写经,有占穆淡朴之概。篆刻、填词、谱曲无一不精。其书风也别具一格。姚茫父,为光绪进士,精诗文、鉴碑版占器,为时所重。考据音韵诸学亦为世人瞩目。书法亦是信手拈来,挥洒敏 捷,尤擅蝇头小楷,可口书楹联百幅,甚至还有兴趣在铜墨盒面上作画,一时传为美谈。袁克文,为袁世凯次子,对钱币学深有研究,书法有晚明之风,楷书则有王 铎之意,旅居上海多年,也是一位风流倜傥的才子式人物,文士型书家的基本特征是:皆不以书法为专攻,也不屑于深钻学问,而是在艺术领域中广泛涉猎,偶出书 法却不同凡响,在风格上有特殊意义,而与正统的书家相去径庭。因此,他们是一批崇尚趣味、知识结构较开阔但于书法不作专门探究的类型。
当然,我们也许还可从此中拉出另一个子系统:画家书。如陈衡恪、齐白石、正震、陈半丁、高剑父等等,这些艺术家在画学方面有着第一流的成果,在 书法上并不专门化功夫作钻研,而是如同作画一般,随手点染,颇有新趣,有时也看不出有什么固定的书法师承。在此中,有完全师心自用的如齐白石、高剑父,也 有较为尊重古典的如写一手米芾风格的陈半丁,其间也有很大的差别。另有一位十分诡怪的徐生翁,身处绍兴一地,不与世往来,书法从颜真卿人手,后来广掺秦汉 至魏碑,稚拙可爱、风格诡异,如不习字者所为,而细察其精品,则横空黉古、不可一世,有着强烈的个性,时人号为“孩儿体”,褒贬参半。徐生翁虽不以画擅 长,但他的书法以趣胜,我们既可以他为赵之谦的滑和李瑞清的涩的对立面:生,又可以他作为崇尚画意的一种书风尝试。事实上,指徐生翁为画家书,至少在形式 上是不会令人感觉太过突兀的。
在民国前期的书坛上,我们除了从书家方面寻找到许多有趣的例证,以及从清末民初的时代鼎革中发现它与书法仍然密切相关之外,还有几个十 分重要的问题也不可不涉及。如果说,从民初的张勋复辟到郑孝胥的伪满洲国,是本时期社会斗争、反封建斗争特别是民族斗争在艺术发展中留下的外部痕迹的话,那么,就书法本身而言,它自身较为狭小的专业环境也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寻源于文化哲学意义上的东西方文化碰撞以及西学东渐等等,而是来 自一个绝对“物质”的前提。
首先,是甲骨文的发现与被引进书坛。
1899年即光绪二十五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了商代甲骨文字。最初,是小屯村农民翻耕棉田之际偶然发现的。此后,它首先成为贩药材掮客用以 牟利的“龙骨”,后经王懿荣等人的揄扬,成为人们注目的对象。1903年,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刘鹗著《铁云藏龟》出版。1905年,孙诒让著《契文举 例》成书。至此,甲骨文才从药材商于小进入文化人的学术生涯,并作为上古文字体系构成厂一个盛极不衰的“甲骨学”。一些文化名人如罗振玉、王国维、叶玉 森、郭沫若、董作宾、胡厚宣等相继成为此中专家。在最初,尽管它已经超越了王懿荣的认识局限,成为一门学科,但还是属于古文字学的一个分支,并未完全进入 书法艺术领域。但这种情况很快即得到了改观--书法在历史上从来与文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荣俱荣,不分彼此。而甲骨文本身也已具备了空间造型之美,它 为书家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又是同系统内的艺术模式。前者保证了它的时代价值,后者则使它变得和蔼可亲易于接受,因此,以甲骨文人书者不断崛起,专家们如 岁振玉、孙海波、董作宾当然是热心于此道者,即使是遗老如前清举人孙儆,也乐于以卜文入书,成为造诣极高的甲骨文书家。直至今日,这种对甲骨文书法的钻研 仍然不稍衰歇。
与甲骨文字同时辉映的,是西北汉简的出土。自本世纪初在新疆和甘肃敦煌出土“流沙坠简”以后,1930年在内蒙古又出土大批汉代木简,世称“居 延汉简”,以后时有出土,蔚为人观。数以万计的汉简出土,为书法带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清季以前,对汉代书法的认识依据一直是汉代众 多的碑刻,金石易于传之久远,但金石之刻在当时义必然“歪曲”原有的书写形态,古代书家们以碑版书作为依据,既是一种审美的需要,又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 择。对于汉代书法究竟原貌如何,大都难置可否。大批西北汉简的出上,正是从物质材料上提出了第一手的证明。它使后人看到了汉代人真正的手迹,并从而窥出了 手迹转换到石刻的种种“歪曲”失真的程度。
有趣得很,汉简中大量墨迹的出现,并没有很快使书坛为之倾倒。以汉碑石刻为正宗的观念仍然牢牢控制着书法家的风格取向,几乎没有人在作品中表现 出对汉简书风那轻捷流畅趣味的钟情。至多,我们只不过在各家学汉碑的作品中看到对剥蚀刻凿的有意忽略,但一写汉隶,总还是求其堂皇之气而较少研究其细腻转 折的用笔技巧与用笔节奏。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当时距离清季不远,强大的碑学风还具有第一流的笼罩力。在行草书中还有些许松动的余地,而在篆隶碑版书体中却 很难改观吧?直到当代书坛,我们才开始看到对汉简书风的追求热情。除此之外,第一批汉简是1899年由瑞典人斯文赫定于敦煌发掘而得,这使它离习惯上的中 国文化层距离较远,要进入书法创作也更为不易。此后在1930年由西北文化考察团所得的居延汉简一万多枚,虽没有这种隔阂,但却逢着中日之间即将发生战 事,书法要想有所发展也不复可能。诸如此类的困境,使汉简书法要进入现代书家笔下变得十分不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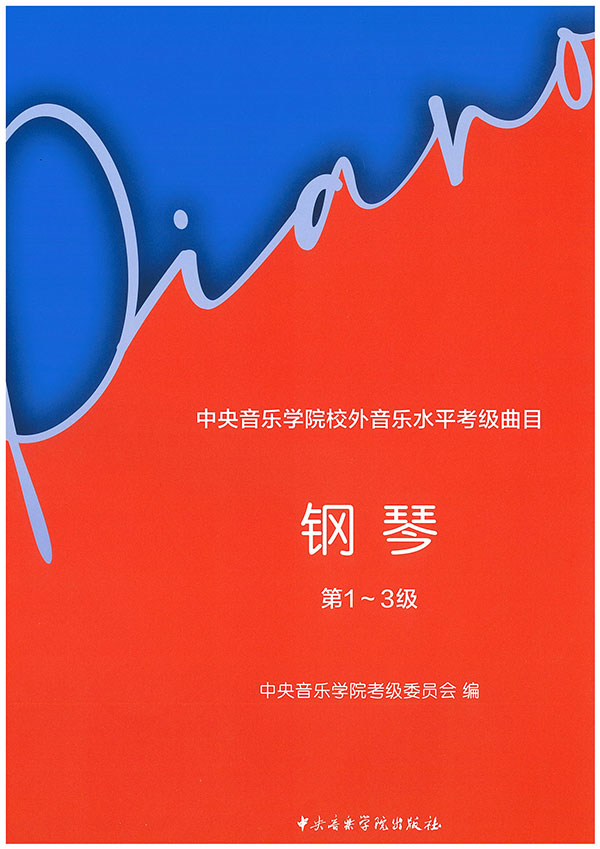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