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话(近代)
再一个是敦煌晋唐写经的面世。
1900年即光绪二十六年,甘肃敦煌千佛洞中沉睡几千年的自曹魏至北宋的经卷文书首次被发现面世,据考,这是在十一世纪初西夏人征服敦煌之前保 存在此的文书,其书法自成一系。但这批珍贵文物在当时即被法国人伯希和、匈牙利人斯坦因和日本人大谷光村探险队所得。除部分为我国收藏外,许多流散国外如 英、法、日等。敦煌写经的书法曾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之中,首先,它是抄经手们为谋生或事佛所为。谋生者是平民、事佛者是僧侣,与书法惯处的文化层相去 甚远,且抄经要求一定的量的限制,其意不仅在书法之美,这又使它可以游移于时风之外,较少受到时替世移、书风嬗递的种种影响,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说它代 表了一个特殊的系统。
但同样地,尽管写经书在书法艺术上令人叹为观止,但它也没能有效地影响民初书坛。写经书与竹木简书的作者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下民,这使一般学子很 难对之作深入了解,而写经书法又类皆工整精到,笔画细劲,作大字并不适宜;以之抄书虽好,却又为民初士大夫们所不屑。此外,经生书卷多为外人所获,这也使 得它在“敦煌学”中广为人注目,却较少引起书法家们的垂青,它作为资料仍然较具有学术色彩而不是艺术形式启迪的。直到当代,才有一些青年书家注意到了它的 风格价值。与此境况相同的,是1942年在长沙楚墓中出土的楚帛书,从风格上说,它也很有特征,但出土后也还是孤嗣绝响,并没有多少人从书法的角度对它作 出估价。
甲骨文、西北汉简、敦煌写经在本世纪的面世,既是古文化研究史上的大事,也是书法艺术研究中的大事。它们之所以没能立即在书法界产生影响,完全 与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止的生态环境有关。但它们的存在仍然令后人振奋,与诸如沈曾植、吴昌硕、康有为以及众多的遗老书家群、文人书家群、学者书家群 乃至尚北碑崇唐碑的各家各派相比,它们显然是完全来自民间的,不具有多少文化阶层的气息的,因此我们指它在理沦研究卜有价值。但随着时替风移,它们会在书 法创作中投射出日益明显的风格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纯民间的这些出土古迹作为一个存在事实并没有影响跻身于文人阶层的书法,而被绘画界大量引进的 西方绘画(其中当然包括一些较抽象的作品)作为一种存在事实,也同样没有从横向上影响纯民族的书法。是士大夫式的、又是民族的,这两个基点的稳固确立,使 民初书法从总体上说完全是-个自我封闭的系统。它很少对外采取开放与接纳态度;它只在发展内部寻求到承北碑或承唐碑的嬗递对应,即使是沈寐叟和吴缶庐也不 例外。故尔,我们又对沈、吴的成功更感可贵,他们并不仅仅是以简单地在形式上汲取外来格局而一鸣惊人;相反,他们是在背负着沉重的传统包袱、靠自己的毕生 心血开创出大师的局面,相比而言,后一种途径更难成功。
三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末,中国社会在战乱中动荡,书法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化形式,也经受了十分严峻的考验。而且,相对而言绘画与音 乐的生命力更强,抗战前期救亡运动涌现出的大量歌曲和版画作品即是明证。而书法篆刻却因其天生的风雅闲适,在大动荡中不时显露出它难与时合的“孤僻”性 格,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事实上,只要书法开始步入现代艺术的殿堂,或者只要书法开始逐渐被从士大夫书斋中移向现代社会的文化机制中,它就会在各种社会 环境中协调自身,寻找生存的机会,哪怕我们只看到它表面上的“背时”与落伍也罢。
三十年代初的书法构成是颇有深意的。如果说,在吴昌硕于1927年谢世之后,他的影响并未受到大的冲击,由于王震、王个簃、李苦李、渚乐三等人 的传承,也由于他在绘画、篆刻方面成就的横向影响,他仍然牢牢站在书法艺术风格史的前端的话。这种权威书风的控制力,由于年代的渐递渐远而逐渐成为古法、对当时的书风而言也渐而产生了陌生感。在这种情况下,三十年代初的书坛是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转换作用的,也即是说,在告别吴昌硕时代之后,书法界迎来了双峰 对峙的新格局。
于右任倡导标准草书从表面上看,应该是一种以切于实用再加上有限的美观的一般尝试。它在中国文化界的反响,应该有类于钱玄同的 文字改革,与书法却并没有太大干系。但切磋草书本身就已包含了一种书坛革新意识。最后,于右任还推出一个草书大家王世镗,显然也使人感受到一种明显的草书 至上气息--王世镗的章草是非常具有艺术气质的。至于他所办的《草书月刊》,从所收论文来看,也基本上是书法研究而不是文字改革研讨。
以于右任当时的政治地位,以1926年他出任陕西国民军总司令后又任陕西省主席,其后则屡展出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等显赫职务,我们可 以肯定他在书法界也有着不同凡响的号召力。没有他的威望与职位,标准草书运动未必有如此的声势,他要连续出刊《标准草书》、《草书月刊》也未必能如愿。因 此,于右任在当时是实实在在构成了一个核心。他以北碑的方笔入草,独具风格,也使得他作为一派领袖拥有一个风格上的保证。
另一个较大的系统,是稍后于他的沈尹默。
正当于右任在纠集同志研究草书时,沈尹默于1933年举办了第一次个人展览,展出作品达一百幅。沈尹默真正呈现出组成流派趋势的时间,应在他举 办个展的五年以后。1937年沈尹默开始写论书诗。1943年,他开始真正致力于书法研究,并撰出《执笔五字法》,这一时期的沈尹默周围,已经聚集了一大 批人材如乔大壮、汪东、章士钊、曾履川、潘伯鹰等,初步形成了流派的雏形。相比于于右任的有刘延涛乃至王世镗而言,沈尹默周围的这批文化人素质甚高,他们 相聚也不仅仅是为了一个明确的书法宗旨,正相反,他们的聚会是一种文人雅士之间的唱酬,文化气息甚浓,与文化界自然也更息息相通。
从风格上看于右任与沈尹默两家的差别,集中表现在于各自对传统的理解角度有异。于右任虽致力于草书,但他自幼潜心魏碑,即使在戎马倥偬之际,仍 致力于搜求北朝碑志与造像记,著名的“鸳鸯七志斋”中所藏三百方碑石,即是他多年经营所得。“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是他当 时的自我写照,而这种刻意显然是与清末以来上承碑学风气一脉相承的。虽然后来于右任致力于草书,但他也还是出以方劲斩截之笔,作品恢宏有大气。因此,这是 在清人所没有的草书领地中实行清人尚北碑理想的一种尝试,它的开拓性毋庸置疑。沈尹默却正好相反,他丝毫不理睬康有为的卑唐说和沈寐叟、李瑞清以下的北碑 派影响,潜心从唐碑人手。或许,是由于于右任的疏忽,他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无法展开的途径。因此本来可以成为北碑派存在标志的标准草书运动并没有按他本人所 预期的那样稳步发展,而《草书月刊》在抗战后的1947年复刊印了三期,1948年又印了一期之后,即渐渐被人们所淡忘。应该说,这四期的《草书月刊》视 野已不仅限于推广标准草书,而是成为一份研究草书的专业学刊。这既证明了于右任及其同仁们的眼界大为开阔;同时也证明标准草书自身的先天不足--仅仅是为 了“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目标,一期刊物的存在足矣,不从“尚北碑”这个风格视角上去评价于右任的成就,他在书法界永远找不到大批追随者。
沈尹默在这一点上精明得多。他在学书伊始即举办个人书展之举,表明他并不以书法的实用性为满足。待到西去重庆、积聚了一批基本力量之后,在他于 1946年返回上海之际,短短两三年间,他俨然成为崇尚二王一系的盟主。一些在三、四十年代曾活跃一时的书家如马公愚、邓散木、白蕉等,相继会集在上海,并借助沈尹默作为文化名人的威望,掀起了一场真正的回归二王的书法运动。这场运动尽管与横向的绘画界相比在观念上仍较落后,仍然停留在缅怀古法的层次上,但却已摆脱了于右任的实用立场,因此,它相对而言仍较有发展前景。特别是那些与沈尹默志同道合的海上名家如马公愚、邓散木、白蕉、潘伯鹰都生活到解放后的 六十年代,而于右任又在四十年代末转赴台湾,遂使沈尹默一系的崇尚二王风在经历了三十年代的初生、四十年代后期的成形之后,一直把它的影响伸延到解放以 后,成为建国以来唯一一支成员稳定、流派特征明显、宗旨明确的创作集群。此外,值得深思的还在于:从现象上看,具有主动的流派意识、并在一起步即宣布明确 的宗旨的,倒是于右任的标准草书运动,因此,它本来是可以构成一个真正的书法现代化运动的。只是很可惜,它的立足点的选择错误使它缺乏进一步发展的能力罢 了。而沈尹默的从重庆到上海,聚集在他周围的书家们并没有很强的使命感,他们想得更多的是吟诗作赋,书法只是余技而巳--这虽然是个不太理想的观念起点,但却是比实用高一层次的起点:有如文字学家未必能参与书法,而旧时代的文人墨客却大多会几笔兰竹或行草书一样。因此,沈尹默等人在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明确的 流派意识,也没有宣布过与众不同的书法宗旨,是相同的审美趣味和不约而同的崇尚南帖立场,使他们走到一起来,并不知不觉地构成了一个轮廓清晰的书家集群,并与于右任的标准草书加北碑风拉开厂距离。
民国中后期的中国书坛是一个构成十分丰富的领域。游移于他们两系之外的书家仍不可胜数。粗粗作一归类,则可划出另两类书家群。一类,是带有浓郁 学者风的书法。以马一浮、张宗祥、余绍宋、马叙伦、容庚等为代表,其特点是风格不激烈强悍、强调内劲与含蓄蕴藉、形式感不强却很自如,因此,大都与于右任 的北碑派书法在表面形式上相去甚远,而较偏于沈尹默一路的江南趣味。但反过来,这些书家的作品又不同于沈尹默一系的路数清晰可按,他们不固定地师承晋唐名 家,只是信手拈出,因此从二王一系看来,又不能说是笔笔皆有古法,甚至有时也有与古法完全不合者。马一浮的书法如不食人间烟火气,谢无量的书法则平正稚 拙,不求表现,最有趣的是柳亚子,自称作书为平生最短,只是信手写去,不问可识与否。像这样一些书家,完全是凭在学问的积累与才气自发而为书,因此,他们 又时常为号称正统的沈尹默一系所讥讽。另一类,是带有浓郁的画家(或更确切地说是注重视觉艺术特性)风格的书法、以黄宾虹、丰子恺、钱瘦铁、潘天寿、来楚 生、张大千、吕风子、吴湖帆等等,这些书家大都以画闻名,他们作书较强调形式美,气度也较开放,挥洒自如,纵横不羁,无丝毫稳健妥贴之感,却很强调抒发性 灵,表情达意。如黄宾虹的风骨、钱瘦铁的生辣、潘天寿的斩截、来楚生的圆畅、张大千的欹侧等等,都是这类书法中的典型。当然,在他们之中也有较近传统书法 趣味者,如黄宾虹与来楚生、吴湖帆等,但从总体看来,这是一些较有“反骨”、不屑以晋韵、唐法、宋意等古人路数自囿的特殊人物。因此他们显然不同于沈尹默 一系的艺术观。但同时地,我们也并不认为他们与于右任一系有什么相近之处。仅以重外在形式与崇尚气势而言,黄宾虹们与于右任有相同之点;但于右任的追随北 碑基本上还是立足于书法本体内部的嬗递,他本人又如此注重草书的实用性;而上述书家群却全然不考虑实用,即使文字书写不准确、只要形式上可取就算成功。故 尔,他们完全是站在书法系统的外部来介入创作的,黄宾虹与来楚生们还有一种本位意识,其余诸家对本位所带来的束缚更显出不耐烦的神态来。
在上述两个书家集群之外,还有一些成就突出的重点人物也不可不提:叶恭绰(1881-1968),字誉虎,号遐翁,早岁从赵盂烦出,后遍临各家 碑版,从苏东坡得益最深。大气磅礴,点画精到,是当时异军独起者,在当时允称大家风范。溥儒(1895-1963),字心畲,号西山居士,出身清皇族,作 书从柳公权人手,上溯二王,有晋人雅韵,骨格尤为清鲢。在当时的北京是声誉极高的文化名人。与郑诵先等共为北方书坛的台柱人物。王福庵 (1879-1960),原名寿棋,宇维季。幼承家学,工篆刻,作篆书工稳劲健,曾为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创隶书新格,去蚕头雁尼之态,以占穆为尚,后 人称力熔篆隶为一炉,与赵时钢(1874-1945)等同为海上书林中较工稳一派的代表人物,除此之外,当时新闻出版界中也涌起一批擅书的名手:如黄葆钺 的古隶,王钝根的行书,皆颇有可取,他们大都是为各家书局的书刊或字帖题签,因此虽非正统书坛中人,但在社会上却有很大影响。再如唐驼的招牌字,虽非大手 笔,也曾在书坛中为人传称。民初的南社中有一大批文人,在政局稳定后也转向书画,内中出了不少书法上的好手。
新出土的书法实物对现代书坛仍然没有什么影响。尽管直到1930年,居延汉简、罗布淖尔汉简也刚刚被发现;1942年长沙还出土战国楚帛书,在 风格上都具有启迪意义,但书家们对此似乎仍持漠不关心的态度。正当罗振玉、王国维在著述《流沙坠简考释》等文字整理工作时,却没有人从书法角度发掘它的价 值。这一方面说明书坛的嗅觉太迟钝,对比出整体上的落伍;另一方面也说明出土文物还只限在考古界,尚未进入真正的文化史研究与艺术研究领域。
正当抗战之际,各地文化人避居重庆。1943年4月2日,在重庆中央图书馆内发起成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全国性书法组织“中国书学会”。成立这样 一个组织当然有许多因素的促成,如果没有战争的逼迫,使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书坛名人都聚集重庆,这样的活动当然很难开展。但倘若没有重庆在当时的相对稳定,书界要有此举也未必能如愿。更有价值的还在于,在中国书学会成立后的三个月,一份杂志《书学》已出版面世。到1944年7月,更是成立了《书学》杂志社,以沈子善任总编兼社长。这一事实意味着书法界开始意识到学术刊物对团体本身的重要性。没有舆论阵地,即使是全国性的书法组织也会缺乏凝聚力的。但是很可 惜,在二年以后的1945年9月抗战结束,文化名人返回各地,这份杂志只出到第五期即宣告结束,“中国书学会”也处于自然解体的状态。
与在组织上的反应迟钝相比,书法从文人书斋走向展览会的趋势却在有增无减。这也是书法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具体标志。自1914年上海举办《吴昌硕 书画篆刻展览》--作为严格意义上的个人艺术展览,它是与如上海书画公会或西泠印社成立搞的展览有截然不同的性格的。1928年,为纪念吴昌硕谢世一周 年,又举办了《吴昌硕书画展览》。此后,书法方面的展览此起彼伏,直到四十年代初在西南二隅,还有如郭沫若书法、傅抱石绘画联展(昆明·1944),柳亚 子、尹瘦石诗(书)画联展(重庆,1945),沈尹默等五人书法联展(贵阳·1945)等等,及胜利之后沈尹默东归,还在上海与沈迈士举行书画展览 (1947)。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傅抱石曾去日本东京举行书画篆刻个人展,还有随后的钱瘦铁在京都举办书画篆刻个人展。这是中国艺术家到日 本去举办展览,在1934年前后的两国关系中,不可谓不是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举动。此外,在日本占领上海的1943年10月,也还有黄宾虹的在沪同好为他 举办了黄宾虹书画展,凡此种种,都可以看作是书法走向社会、走向展览厅--从而逐渐消除原有的雅集清玩性格的成功例证。黄宾虹是个很特殊的人物,他几乎参 与了当时中国书画界的绝大部分活动如展览创作、兴办艺术教育以及学术研究、新闻出版等工作,从他身上,可以窥出民国这四十年间书画活动的许多珍贵内容。
展览的出现还给艺术家的观念带来了莫大冲击。强有力的悬挂壁上公诸于众的形式,使文人书斋信手拈来变得十分落伍。一幅展品必须在形式上有吸引 力,这是一个古代艺术家所不太关心、而现代艺术家必须引为首要的要求。由此牵动的对书法、篆刻创作的观念标准乃至创作心态诸课题,将意味着对整个中国书法 进行重新认识的严峻现实。此外,社团活动也使艺!术家们的组织走向多元构成。1917年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社的成立,即标志着社团活动已从一般的文人阶层走 向各个更具体的专门阶层。在大学中出现这样的组织,对书法未来发展的启迪作用与历史意义不可估量。
这个时期,在书法发展机体的内部,我们首先却看到了一种观念的震荡与自我调节。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我调节带有很明显的“被迫”色彩,调节的理由并不是来自书法发展的艺术轨道内部,而是来自两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泛文化领域。
首先,是书写工具的改变。自本世纪初钢笔被引进中国之后,关于钢笔与毛笔、舶来与传统、国货与洋服“万年笔”之类的争论很热闹了一阵子。对反对 钢笔书写取代毛笔磨墨方式既不应简单地斥之为是陈腐与落伍;而对毛笔书写的退出实用领域也应作全面的估价,至少,它带来了一个以前浩瀚千年书法史从未遇到 过的新问题。
钢笔被引进中国、并以其使用便利的独特优势迅速占领书写的实用市场;势必把书法逼到一个非常狭窄的窘境中。书法在一瞬间充满了迷惘,它对自身存 在的必要性产生了不可名状的怀疑。钢笔书写的出现却逼迫书法家在两者必居其一的立场选择中明确表态:虽然它并没有在审美形式上与传统书法上分庭抗礼的企 图,但它的悄声占领了实用领地,却使书法家在原有的书札、明信片乃至公文告示等领域中无所事事,以方便、迅捷的观点去看,传统书法的一波三折、藏头护尾当 然远远不及钢笔(硬笔)书写拥有优势。这种严酷的“适者生存”原则曾对书法构成巨大的冲击;书法原有的领地被侵蚀、被并吞,但它也迫使书法家们反省自身。由于钢笔书写作为一个严峻的反面参照,传统的书法艺术势必以有别于它作为自身生存的前提,这又意味着它不可能再跻身文字书写、像过去那样使审美与记事平分 秋色。
因此,传统书法的被从实用中驱逐、其地盘被侵占、其泛文化(文字)价值的日遭削弱,倒是从反面纯化了书法本身。作为一个过程与现象,它是毫无准 备、仓促上阵的,因而也是十分被动的,但作为结果,它却获得了几千年书法历史望尘莫及的绝大好处。依靠环境变革和整个文化变革的外部提携,它寻找到了一个 十分有利的突破口。
另一个问题,是在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汉语拼音化运动与文字改革运动。伴随着白话文在新文化革命中的主导地位的确立,汉语--汉文化的结构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变化甚至冲击了作为汉文化的语言学科的最基本单元。
钱玄同公开提出废除汉字。一九二二年《国语月刊》汉字改革专号中,钱玄同宣称:汉字“最糟的便是它和现代世界文化格格不入”;在教育部国语统一 筹备会第四次年会上,他还提出了《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提倡汉语拼音文字应采用“罗马字母式的字母”,要清算“汉字的罪恶”。应该承认:以钱玄同 作为文化名人、北京大学教授,又是教育部组织的“汉字省体委员会”的首席委员,还有《国语月刊》作为舆论阵地呐喊助威,说它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文化思潮,是 不为过分的。
置身长期封闭环境和经受深厚文化传统陶冶的书法家们,在这个严峻关口中几乎保持不约而同的态度。他们自知在书法独立与整个文化进行对抗的对阵中 决无获胜的希望,因此他们大都对文化改革采取沉默的立场;他们可以在书法以外积极投身于新文化、新政治运动,但一旦遇到针对书法所出现的压力,却无不“王 顾左右而言它”。于是,这造成了一部分书家的双重文化性格:在文学、美术、学术方面的领先与在书法中的稳健成正比。但值得深思的是:在书法中并没有赶时髦 的投机家,纵观整个民初书坛,竟至找不出一个稍稍前卫的激进派。而令人发噱的还在于,像于右任在书法上能提出“标准草书”问题,从主观动机上说并非没有一 种领袖书坛开创新格的意识--相对于令人昏昏欲睡的遗老们而言,这是很有现代色彩的尝试,与绘画中的林风眠、徐悲鸿的积极开拓在动机上相去无几。但他的主 观一旦落实到具体,去选择草书标准化的研究目标,却又使人倍感迷惘。对现代书法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我们已经从上述诸方面获得一个大概的轮廓,有 关书法发展过程中内部自身的逻辑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加以检讨。
(一)相对于现有的书法立场而言,民初的书法观显然带有浓重的传统实用目的,这本来是自秦汉魏晋以来书法理解的正宗,到了清初,这种实用性格又 被掺人了金石考据诸学的学究色彩--它的实用性并未有丝毫的削弱;而它作为书法艺术表现的认识萌芽,却被更广泛、更浓郁的学术研究立场所淹没。
(二)沿袭着乾、嘉以来金石考据学派的传统,民初书法走的基本上也还是复古主义的老路。
(三)深入到民初书法的艺术哲学观立场,我们看到的是又一种平淡与稳健。在绘画、戏剧、文学都在积极反思自身、希望改变其旧有的传统观念立场,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认识、重新注释的同时,书法却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反思的必要性。
(四)遍观民初书法家自身的素质构成,我们也还是看到了一种“同步”现象。在面对书法这个共同的对象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传统型的,具 体表现为士大夫式的雅玩态度,对书法抱着一种有距离的赏玩态度,将它作为一种手段;另一种是现代型的,具体表现为艺术家式的表诉态度,对书法抱着一种发白 内心的表现立场,将它作为一个目的和归结。
(五)从对艺术的思想方法来看,民初的书法篆刻家们完全缺乏真正的艺术理论应有折思辨性格,他们思考问题习惯于以“写字”为起点而不是“艺术创作”为起点。
(六)只有一个方面是例外,让我们看到了令人振奋的一线希望。这就是在书法篆刻界开始出现了社团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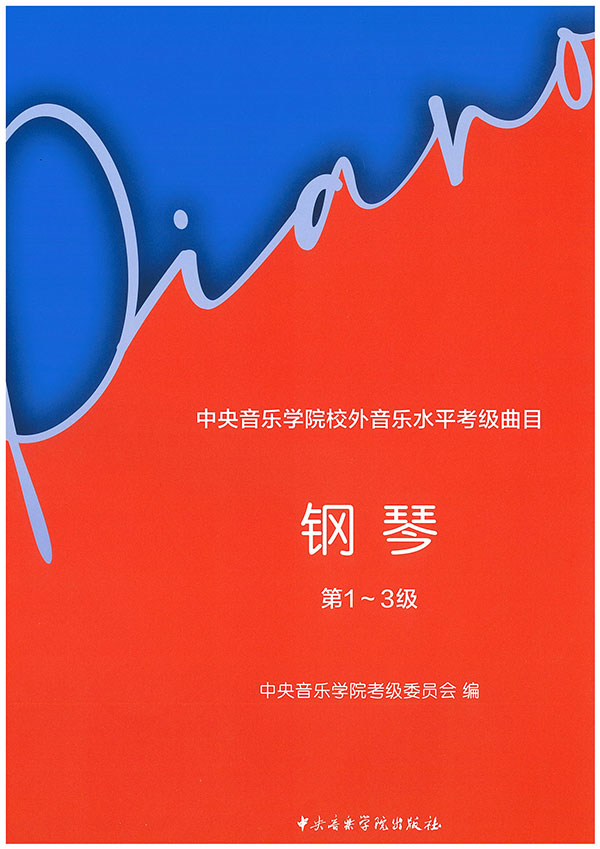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