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话(魏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南北朝——书法的自觉时代
魏晋时期的书法家以及他们创制的风格样式,一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古典书法艺术的主流。无论后人怎么以法、意、态、势来概括和区分唐、宋、元、明、清朝书艺的时代特征,其风格依然是以魏晋风韵作底蕴,为归宿,从而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魏晋现象”。
魏晋时期,按历史学的划分,自魏文帝曹丕建国(220年),至东晋恭帝逊位禅让(420年),前后达二个世纪。其间,有文献可征的书法家,近二 百人。真正能影响规约后世书风的大家,当推钟繇与王羲之。其他如擅长古文篆书的卫觊、邯郸淳,精通行书的胡昭,以题额榜书见称的韦诞、梁鹄,章草圣手的皇 象,今草名家的卫瓘,索靖,由于名迹罕有或者不传,虽然声望彪炳书史,对后世的书艺发展并没有实在而深远的影响,即使在去其未远的东晋,因为钟王盖世,朝 野争相效法,影响力已经十分微弱,至多只是强弩之末的余势,一线单传的孑遗而已。形势比人强,谁能奈何得了身后的世风和趋势。
就在钟王披靡东晋之际,意想不到的是王献之异军突起,咄咄逼人。在东晋末年至南朝宋、齐之际的一百年间,居然迅猛地形成了推迈钟王而独尊王献之 的局面。这种局面,南朝梁陶宏景在《与梁武帝论书启》中说得最为透彻具体:“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钟繇)继以齐名,贵斯式略,海内唯不复知有元 常,于逸少亦然。”
王献之作为魏晋书家群体中的一员,论行辈,他是殿军之位。论影响力,却远在众家之上,仅次于钟王。尽管梁武帝、唐太 宗贬抑王献之,唐朝李嗣真却将王献之与钟繇、王羲之以“逸品”同列。王献之以他流美轻盈的书法,为“魏晋风韵”增添了不可或缺的一笔,这是最后的又是最新 妍的一笔。
从殷商甲骨文作为成形中国书法史的开端,到公元三世纪的西晋时代,它已走过了近1500年的历程。在这1500年间,我们尽管不能说书法没有自觉的成份--比如在汉代,之所以能产生像张芝、索靖、杜操、崔瑗这样一大批钟情于已不甚实用的草书的书法家,一些书家的笔下之所 以“反难而迟”,都说明在当时,书法在某些场合或某些人那里已被用作或被赋予欣赏意义--但从整体上讲,它并没有从实用阶段脱离出来、从依附地位解放出 来。魏晋以前,在绝大多人的意识中,书法在功用上仍不出下列数项:歌功颂德、述史记事、谋取功名(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一下赵壹的《非草书》就可感受到)。
真正使书法成为一门完全意义上的独立的自觉艺术,是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一大批魏晋及后来的南北朝时代的杰出书法家、书论家。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书法成为文人士大夫抒情遣兴的工具。
如果说,以二王书法为代表的“晋韵”书风的确立作为魏晋书法的实践上成熟标志的话,那么在这种成熟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保障,就是理论上的自觉。
首先从数量上看,魏晋南北朝的书学空前繁盛。据日本书学家中田勇次郎所著《中国书法理论史》对可考文献中秦汉、魏晋南北朝书论、书目所作编排看,魏晋南 北朝书论竟达40余篇,即使避开真伪尚有争论的卫铄《笔阵图》、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及《笔势论》、《用笔赋》、《书论》和《记白云先生书 决》、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等论著,尚有三国刘劭的《飞白书势铭》、晋成公绥的《隶书体》、卫恒的《四体书势》、杨泉的《草书赋》、王珉的《行书状》、南朝鲍照的《飞白书势铭》、王情的《古今文字志》、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虞和的《论书表》、王僧虔的《论书》及《笔意赞》、萧衍的《草书状》、《观 锺繇书法十二意》、《答陶隐居论书》、陶弘景的《与梁武帝论书启》、《论书启》、庾元威的《论书》、袁昂的《古今书评》、庾肩吾的《书品》以及北朝江式的 《论书表》等等,近30余种,而在此之前秦汉时代,现今有著录的书论不足10篇。书学论著的大量出现,既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空前繁荣的结果,它又反 过来为这种繁荣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保障。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自觉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书法自此开始有了一套包括本质论、创作论、技法论、品评论在内的完备的理论批评体系作为艺术创作、欣赏的依据。在此中间,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一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书论家们从理论上及时而准 确地描述,总结了二王书风为代表的“晋韵”模式的特征和实质,使之成为今后世效法的经典范式;二是魏晋特别是南朝羊欣、王僧虔、袁昂、萧衍等书论家提出并 建立了一套以“意”为核心,将人物品藻与艺术鉴赏合而为一的书法批评模式,成为整个传统书法理论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理论的体系化成为本时期书 学区别于以前书学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
当然,以上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以下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审美意识和批评意识的自觉。在秦汉或更远时代,在人们的意识中,书法更多地是一种汉字的书写行为,对其即使有审美观照,也是个别、零星、分 散的或与对文字之优劣评判纠缠在一起。所谓艺术批评更是不可能。但在魏晋南北朝,不论是对书体美之描述,还是对书风得失之评价,都有人的主动意识的积极参 与,因此书学已不再是“小学”(即文字学)的附属品或补充,它日益成为一种专业学说走向理论的前台,这一现象直接导致了本时期书法美学研究的兴盛和书法批 评活动的繁荣。
二是专业书法理论家、批评家的出现。按照中国书法的传统,书学论著一般由书法家自己撰写,但魏晋特别是南北朝,许多以书论闻名的理论家,如虞 和、杨泉、王倍、鲍照、庾元威、江式等,并不以书法创作出名或书法水平并不见得多么高妙,他们的理论并不单纯地是实践的一种总结,而更接近于纯理论的研 究。这种现象的出现打破了单一的以创作家代替理论家的落后状况,使得实践与理论出现分化,从而使书法理论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
综上所述,书学论著数量的丰厚,审美意识和批评意识的主动参与,书法理论的体系化以及专业书法理论家的出现,构成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理论的四大主要特征。当然这些特征又是依据于魏晋南北朝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政治、文化及心理背景而形成的。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充满腥风血雨、纷争离乱、动荡不安的时代:曹魏代汉、司马晋代魏、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王敦苏峻之叛等等,接踵而来,灾祸不已。这是一个崩溃的时代,旧有的政治、社会、经济秩序和意识道统分崩离析,人们痛苦不堪。
但同时,这个“礼乐崩坏”的时代又是一个重建的时代。
中国社会自公元前三世纪由秦始皇削灭六国建立秦帝国至公元三世纪的东汉末叶(进入战乱的三国时代以前)的六个世纪中,中国一直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帝国。这个帝国因西汉中叶武帝时期的大儒董仲舒的一套“天人感应”学说而变得精致、“神圣”。
在那部足以堪称封建专制统治“圣经”的《春秋繁露》中,作者董仲舒通过“竭力把人事政治与天道运行附会而强有力地组合在一起。其中特别是把阴阳家作为骨 赂体系构架分外凸现出来,以阴阳五行(‘天’)与王道政治(‘人’)互相一致而彼此影响即‘天人感应’作为理论轴心”,从而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人特有宇宙 观和思维模式,维护大一统专制集权制度的理论体系。
在以“君权神授”观念为核心的“天人感应”说中,一切的封建秩序都被绝对化、神圣化,就如同皇帝的权力来自上苍一样,臣民只有认同并绝对服从的义务,对其任何的猜疑都是一种犯上作乱的逆行。
--过分突出君王、过分强调秩序、过分注重群体,使得一切游离于那个森严的等级、秩序之外的生命、感情、思想统统成为有悖于“天理”的“奢望”和异端。
正是于此,在整个秦汉时代,不可能有“文的自觉”、“艺的自觉”、“书法的自觉”,因为此时尚不具备自觉的基本条件--人的自觉。
然而,在董仲舒的这种“天人感应”说统治中国近三个世纪后,那片古老而悠久的东亚大陆上最为强有力的政权--汉王朝开始崩溃,中国社会进入一个 纲纪颓弛、国是日非、英雄迭起、匪夷横行的离乱时期。此时,被董仲舒们神化的一切权威、秩序分崩离析。权威与秩序的崩溃,带来一场思想的强烈“地震”-- 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继春秋战国后)的第二次“礼乐崩坏”。面对这种崩坏,东汉的士大夫们一个个心急如焚,纷纷挺身而出,改弊匡失,舍身为国。与腐朽势力进 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然而面对士大夫们的一片赤诚,皇帝不仅没有被感动,反而一次次向他们举起屠刀,于是成百上千的忧国之士纷纷倒于血泊之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
按照“天人感应”的儒家经典理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然而现在,士大夫被皇帝抛弃,儒学先哲们指明的那条“兼济天下 ”的光明大道已被堵塞,于是他们只有怀着深深的遗憾,走上一条“独善其身”的道路。这样从东汉末期开始,中国的士大夫们的信仰有了不同--从对入世的儒家 学说的深信不疑转为对黄老出世哲学的迷恋,这种迷恋至曹魏正始年间因何晏、王弼等人的努力而形成一种具有浓厚时代特色的学术体系--魏晋玄学,这是魏晋知 识分子自汉末“天人感应”儒学理论衰微后历史地承担起建构新的精神支柱的艰巨任务后结出的硕果。
专注于辨析名理的魏晋玄学,从表面上看它仅仅是一种流行于魏晋时代文人士大夫阶层,用于逃避人世苦难的一种清谈、玄学,然而,在其背后却是“人 的自觉”--文人士大夫从那种君临一切的神权下解放出来,从首先对道统、秩序的关注转为对生命或自身存在的关注。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文人士大夫才敢大谈 “道本儒末”、“越名教而任自然”,甚至厉声痛斥“君立而虐生,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才得以有暇去关注他人的举止、言行;才对生命的痛楚、悲苦有了那么多的感伤。
魏晋玄学作为时代的产物,它不同于两汉儒者看重世俗关系、格守礼法、轻视逻辑思维和论辨的习惯做法,而是充分运用哲理思辨,探究无限,思考世界 和生命本体的存在,因而自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带着浓重而纯粹的哲学理性思辨性质。这股思辨新风给中国传统哲学躯体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玄学思辨之风的兴盛深刻影响了魏晋间各方面的学人。在文学领域内,出现了像刘勰的《文心雕龙》、锺嵘的《诗品》这样具有前代少有的严密理论系统性和深刻美学内涵的理论成果。并且,同时期的科技也有了较鲜明的理性思维的特色。
理性思辨活动的空前繁盛和思辨成果的丰硕,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书学的繁荣提供最为直接的前提条件。当然,这个前提条件却是付出了难以估量的血的代 价而得来的。“死神唤醒了人,而天人感应的权威思想的崩溃又为人的自由发展去掉了枷锁。因此造成了人的自我意识的增强,精神生活的丰富和独立人格的追求,这无疑是人类发展的一次大的进步。”
中国书法的全面自觉,正建筑在这种进步,这种思辨,这种空灵之上。
- 上一篇:中国书法史话(西汉)
- 下一篇:中国书法史话(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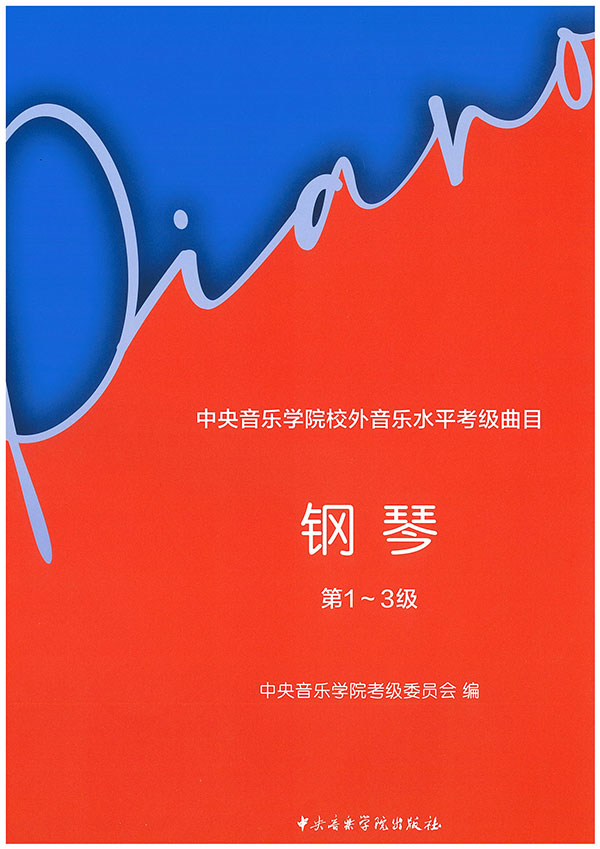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