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如轩书法随笔
七、遥寄刘新德
我的心中一直有个遗憾,就是没给新德兄写点什么。第六届全国书展时便已承诺,直至如今仍未兑现,想来多有惭愧。
新德兄生于齐鲁大地,又迁巴蜀第二故乡,情形与右军夫子类似。若睹其面则没几许山东大汉的感觉,有的更多的是巴蜀人的精明剔透。而听其言则不失鲁人本色,快人快语,直陈己见,尤其是那嘹亮的大嗓门儿,让你对他的山东根性深信不疑。京华连床夜话,至今历历在目。他的字也有两面性,小字随体赋形,舒卷自如,机趣叠出,是巴蜀气质的;大字则开张枯劲,有几分豪气,又流露出鲁人的风度。
全国第七届中青展,新德兄的获奖作品大字对联,展后批评较多,而且多有偏颇之处。真想站出来辩驳几句,终于没有。现在想来,真的那样该是多么愚蠢。批评者是对我们负责任,他们是善意的,完全为了我们好,今天我们身边没有几个畏友、诤友了,批评者是我们的真朋友,他们的坦诚对我们来说多么可贵。我们自己也要学一点儿大家风度,不要一听批评就气炸肺,宽容地面对批评,愉悦地接受反面意见,认真修炼和提高自己不更好吗?我们一代青年书人正应该猛醒,走出书法家的梦幻。在“书法家”称谓如此廉价,满街都是圣人的今天,做所谓的“书法家”实在可怜,何况我们离书法家的距离实在太遥远。我们确实差得太多:功力、性情、学养 …… 没有一样值得炫耀。
新德兄的字太像何应辉和王镛两先生,当然他已有所意识,而开始留心谢无量、刘孟伉两乡贤的东西。这样说似乎应了凡古就好简单庸俗的观点,其实并非如此。从学习的角度,学今人学古人无不可,但就创造而言,入时与泥古同样可怕。新德兄的字的确有点儿过于入时,能够及时调整,足见他聪慧睿智,真希望他潜入更多的古今优秀书家的心灵与杰作,潜入我们民族文化艺术的沃土,从而得以蝉蜕。
建立属于自己的艺术语汇和个性精神实在太难了,尤以书法艺术更难,既要不践古人,又要与今人拉开距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语)何难至哉?这是说来容易,做来艰辛的苦差事,它需要数十年的磨洗与砥砺,古来有几人能渗透和踵至……记得苏东坡有首咏梅诗尤似书法创作的个性要求:“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冰容不入时。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枝。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酒晕般小红桃杏色的春态,故作而无端地绽放在玉肌似的孤瘦雪霜枝的寒心之上,报春而未改寒心,这才是梅格,同样可喻书格。这不是“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孙过庭《书谱》)吗?书法创作是集千家来煮一锅粥,是酿蜜不留花,新德我们这一辈如果能确切估价自己,也只在 “采花”、“乞米”阶段。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朱庆余《闺意献张水部》)。我们不是为别人活着,不必为哗众取宠而描眉打鬓。禅宗四祖道信说得好:“任心自在,莫作观行。”愿与新德兄共勉。
八、读《负暄》三话
纵观当代书法批评,大多要么无原则地胡吹乱捧,要么骂街式的当头棒喝,要么油滑地中庸…… 健康的批评极为少见,这常常使我想起张中行老人。
老人的写人记事散文是大家所熟知的,剔除一切雕绘和藻饰,纯乎篱下闲坐“摆龙门阵”一般,平实之中蕴藉深厚。用坡翁语“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评价当不为过。老人文中多涉及人物的书法评点,虽三言两语,廖廖数字,却公允切当,尤中肯綮。
老人是深识书者,仅就其时与师友手泽摩挲对话,即已深入三昧。何况老人早年在北大读书,“钻故纸堆”,浏览书法文献,以包安吴,康南海《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为导游,参悟碑帖、墨迹(《负暄三话—— 学书不成》),其通晓书法可想而知。而老人却以平常心出之,用“学书不成”、“聊以卒岁”自我写照。绝无时下所谓“理论家”的狂妄与霸气,古人书论尚未读通,读两本西方美学的书还没来得及消化,便肆无忌惮地指点江山,标榜这个旋风,那个现象,比起老人的谨言慎行,实在微不足道,不知是怎样的渺小。
老人于书法品鉴,首先是知人论事,这与坡翁“论书兼及其人生平”一脉相承。书法是书家学问、才情、风度的自然流露,只有深入书家的精神生活,才能评价确当,鞭辟入理。老人评论书法是在状写人物生平中自然论及的,常常是人品、性情、才智、书法相互参证,因而能深入表里。如说太炎先生的字“倔强而不流丽”(《负暄琐话——章太炎》),短短六个字,人奇字古,灿然在目;谈黄节先生的字:“笔姿瘦劲飘洒,学米,只是显得单薄,或者是天资所限”(《负暄琐话——黄晦闻》)。从字迹论及气质性格,可谓当行。
其次就是审美胸襟开放,没有先入为主的偏执。他认为:“像样的法书,风格可以万变(大者流派不同,小者人人不同)”(《学书不成》),且不以个人好恶,否定客观的美的存在。即以他对赵、董的认识便可见一斑:“赵、董同样出二王,二王兼收古之所长而表现为今变,因为内容丰富,所以后世取其一仓一廪就可以成为小康,取什么与时代风气有关,又与个人的爱好有关,同源异流,流得路径越长,面目变化越大。正如欧是取其险劲,米是取其流动,赵、董是取其柔婉;至于功力之深,我以为,欧、米与赵、董是各有千秋”(《负暄琐话——马叙伦》)。分析细致,有理有据,毫不武断。更可贵的是,老人对一向为人所轻视的女性书法(闺秀小楷),给予肯定和重视,更见其审美立场之大,那段幽默风趣的论断尤难令人忘怀:“唐初四家的褚,无论《圣教序》还是《阴符经》,都劲而秀,用《史记〉的话形容,是‘翩翩浊世之佳公子’、还要加上顾影自怜。倪云林则有如山林隐士,也有劲秀,但更显著的是倔强,远离世俗。明清闺秀小楷,风格几乎都是清丽娟秀,看到,使人不由得想到玉楼中人的柔婉。佳公子,山林隐士、玉楼中人,都好,如果不许贪,那就只好把选择之权交给主观,也许因为我是宝二爷所谓泥做的吧,天命所限,我就选了明清闺秀小楷”(见〈负暄三话——闺秀小楷〉)。读来令人忍唆不禁。当代书坛竟尚丑拙之书,秀美一格几被扫地出门,是否应该引起反思。
再次,老人论人评书,不因权威和师友,便顺避缺失,总是得失兼论,公正客观,这是当今理论界所缺少的品格。他敬佩知堂老人⑵的学问文章,但对于他人品的过失不能原谅:“旧事难忘,有时自然会想到,吕端的故事就会涌上心头,也应该算作感慨吧,是惋惜他不能学习吕端,而是与吕端相反,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 ”(〈负暄琐话——苦雨斋一二〉)。字里行间藏着深深的遗憾。评顾随书法:“字学他的老师沈尹默,简直可以乱真,据我看,是锋芒较少而脂泽较多,正是各有千秋”(〈负暄琐话——顾羡季〉)。评张伯驹书法:“面貌清秀,只是筋骨少,过于纤弱”(同上《张伯驹》)。准确精当,实事求是。对民间书法的定位也极中要害,即不举得太高,也不全盘否定,在《马叙伦》一文中,通过唐人写经与马叙伦作品比较,阐明自己的观点:“马先生这件手迹用小楷写,风神确是与唐人写经有相似处,不过唐人写经多经生书,工夫虽纯,终非书家,所以与马先生比,总觉得脂泽有余而筋骨不足 ”。
当代书法批评,混乱芜杂,品评标准已被践踏,甚至是非错位,黑白颠倒,这不能不让我时时想起张中行老人。
- 上一篇:书法随笔:细节未必决定成败
- 下一篇:书法艺术之随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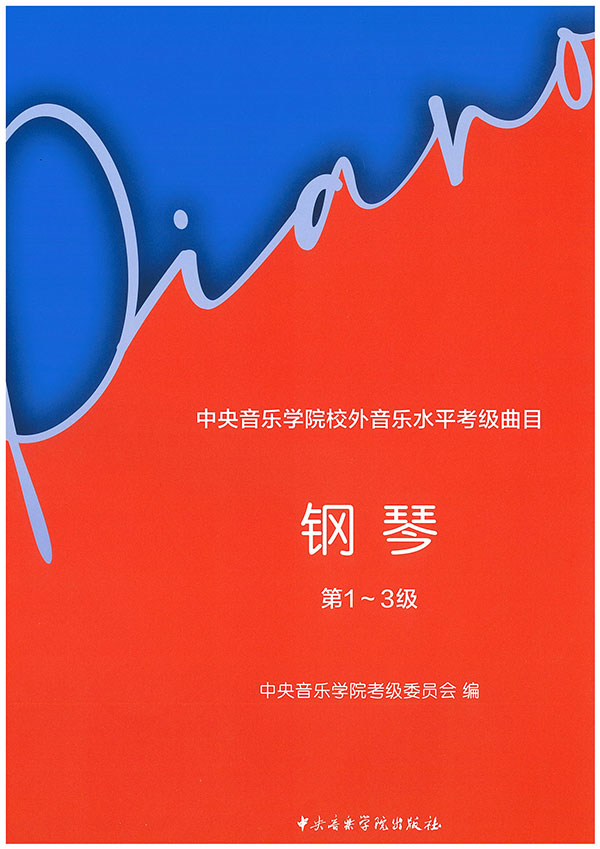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新艺考首考图文实录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北京2024年高招艺术类...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7部影片春节档上映,预计...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解密照明设计与人体艺...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中国著名建筑一览(图...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北京故宫馆藏陶瓷器赏...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